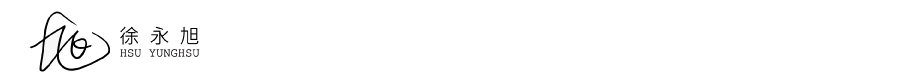界.逾越 / 徐永旭
這是一整個創作期間的狀態
我不喜歡自己生命的歷程是重複的,甚至
是可以預視到將來;生命不是規劃的,它
是自由的、創造的。
自己曾經歷一段有規劃的、規律的生涯,但伴隨著創作的發展,探索生命的本質,也不斷去體驗生命中的不確定,它是自由、創造的本源。和「過度」、「極限」、「逾越」在所經歷中相遇, 讓自身不斷的重生。我從其自身中走出來而發生變化,也反身改變著創作。如果我在創作之前就知道這創作所要表達的,那我就沒有很強的動力來完成它,我之所以要創作就是我還不準確的知道創作所能帶給我的所能讓我思考的,也因此創作影響、改變著我,我也改變著創作,不使自己以同樣的思考同樣的方式來進行創作。
當打開一扇「創作的門」,進到一個無邊的世界,一個宏大、清晰的目標在召喚著我,勇往直前,朝著它前進,我在「完成」。
當打開另一扇「創作的門」,進到一個無邊的世界,是荒漠、是原野、是峻嶺,來時的門不見了,前進的路似有似無、縱橫交錯,探索、穿梭,我在「創作」。
我不是期待我能做出什麼作品,而是在這樣的創作之中能帶給我什麼,甚至我也企圖從創作中來解答心中的種種問題。但卻似乎永遠尋覓不到解答,當眼前即將豁然開朗的時候,卻因為創作是在進行著、生活也停不下腳步、不停的觀看,什麼都是不停的,一切又是回歸到尋找,包括什麼叫自己。當自己選擇泥土來當作創作的媒材,如果拋開材料、技術、工具這些問題時,它和自己創作的關係是什麼?
不斷對自己拋出問題,似乎問題還不斷的出現,但我並不想從思維中立即去解決這些自己的疑惑,我計劃使用創作的行為、過程、作品來作為解決不斷發生在我左右的問題,或許是無解或許將豁然開朗,創作結果的物件只是一種挪用,它不是最終的目的,問題不斷的衍生和創作不斷的進行成為兩條軸線,但他們之間是互為因果關係。
在創作這條軸線上,選擇以「陶」材質本身的感情作為主軸,以極薄極大的方式凸顯材質自身易碎緊張的張力,但事實上我將其定義為「反陶」,因為碰觸這個材質的點是它自身的弱點,但我並不定位為「顛覆」,「反陶」是「陶」異質的思維。這樣定義是一種手段,置自身於困頓,再從其中開顯出來。
我選擇使用泥土盤築作為執行這條軸線的方式,採取其長時間不斷重覆相同的動作,讓知覺以最直接的方式進入創作的行為之中,這期間所產生所有的情緒反應讓作品更直接的表現「我」自身。
因此,我為自己形成一個「規範」:土、不使用任何工具、在我認知之中相對的大與薄,單純的在「圈」的動作中和「圈」的形式中,悠然的像遊戲般的進行。以簡單的手法(兩手主要的手指相同方向的動作)、單純的形式,卻在時間的壓力下(必須在工作室使用期限內完成所有論文展的作品)進行創作,這時外在無意義的物理時間轉化成自身的心理時間,也因此我必須在一個階段內每天長時間用相同的手法重覆相同的動作來進行創作。我也讓這每一件這麼「大」的物件,從底部開始,都維持在這樣「薄」的相同厚度一直到作品整個完成。這為了讓自己在創作的過程之中隨時都維持在相走在鋼索上那種戰戰兢兢的情緒之中,把走在鋼索上隨時面對著當下不能產生有任何慣性狀態(走鋼索的人當一產生慣性時即有掉落索下而亡的危機)透過創作而形成當下的藝術行為。在這樣的情緒狀態之下,又必須長時間反覆相同的動作,自身的心理、生理也不斷出現強烈的起伏,時常感覺已經到達自己所不能負荷的狀態,甚至會出現超越了自己所能負荷的範圍。在這樣狀態之下好似自己在尋找一個「臨界點」,當臨近它時,只要一經過任何一點點的搖晃,種種的許多現象:感覺、情緒都因此而出現。也很容易的從自身之外來檢視這些創作的行為與情感狀態。
在創作進行的階段中,一次懈逅的機會,接觸到傅科(Michel Foucault)晚期有關生命美學的思想,也在這創作之中使用一些方法進行創作主體及自身主體再檢視的方法。
我選擇了使用攝影機,在每天工作最後的階段進行三十分鐘對自己在工作中的錄影,等結束工作之後即刻進行這段錄影的觀看,這時候我是透過鏡頭的攝錄然後觀看放映中映象的自己,雖然是由自身去觀看一個虛擬的自身,但卻是由一個他者的位置來看回自身,這時候自己和自身做了一次的斷裂。在觀看的進行中,強迫自己把時間回溯到被攝錄的時候,觀看的當下去回憶攝錄時工作的當下思維中所出現的任何思想活動,在觀看結束之後,以書寫的方式寫下觀看時所回憶的內容。這時思緒異常的活躍,記憶底層不斷的翻閱,從自我之外一直不斷的和自我對話,後來我將書寫的方式改為錄音紀錄的方式,這種對話與情緒的出現更為明顯與強烈,甚至顯現了過往生命中一直追求而無法得到的情感與感覺。
當隔天再回到工作室繼續創作的時候,一樣的反覆勞動、一樣的緊繃的精神狀態,但時常可以透過創作的過程召喚出昨夜觀看時與其後紀錄時所出現的情緒與感覺,我可以感覺到,透過我的手、身体、泥土,把這種情緒與感覺進入作品之中,而且我也可以再次透過手、身体、泥土,時而清晰時而模糊從作品中去擁有這份感覺與情緒。這種狀態透過創作的行為,不斷的在我與作品之間來回進出,這時候創作與作品已成為我訴說情緒與感情寄託的對象。自身與作品之間已不是主、客體的關係,而是不斷的互為主體,進而為一主體。
在這樣的創作狀態進行之中,作品卻在自己所為它設下的規範:「反陶」,一直長時間無法有完成的物件出現,時常在創作的過程之中或是完成待乾燥的時候崩塌而功虧一潰,但在從新來過的時候,泥土在我手中捏塑又更薄了,等到它不再崩塌,第一個物件完成的時候,已經耗去了我在這工作室所能工作做時間的三分之一,也因此時間的壓力已是加倍的成長。
當有物件完成之後,下一個物件開始進行時,為了不要因為慣性而讓這種身體感與情感發生減弱或消失,回到完成的物件中檢視,在我認知的條件之下,抽去了可以讓作品完成的安全因素,開始進行下一個物件,或許接下來也在半途崩塌,或許在緊張狀態之下完成,但得以讓身體的處境與情緒的發生更加增強。這種感覺好似我站在一疊直立的磚塊上,一次抽掉腳下的一塊磚,一次一次的,到最後我會站在什麼上面呢?
作品出現的形式:在前述的條件之下,不斷出現在我的映象之中的任何形式我將會形塑而出,但我不使用橫向的造型語彙去關連這階段的創作,在不特定形式下所出現的關連,它將呼應我不斷的提問。
我嘗試表現自身「不確定」的因素——現在與將來種種的一切,我也以「不確定」的模式來進行創作,在作品與我之間來回的表現「我」。
當創作回到自身的探索,感覺一切是那麼的真實又是那麼虛幻,也是那麼的殘酷,但是那種致命的吸引,就像一帖劇毒的麻藥。當探索自身的情緒、感情、內心的一點一滴,像繃緊了全身的每一條神經,一經撥動,似乎不是自己所能承受,但又期待著撥動後所溢出的任何點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