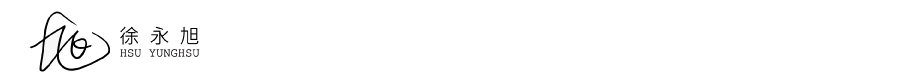序-2005徐永旭雕塑展
1999年在美國紐約州羅徹斯特學院的客座教學期間,與當時剛任教於該校不久的年輕教授Julia Galloway認識,在交談之中得知她在研究所進修期間的第三年,距畢業論文個展只剩六、七個月時,因滑雪而摔斷了右手,因此她無法繼續親手製作完成計畫中的作品,苦惱了一段時期後,她拾起畫筆開始在已素燒完成的坏體上彩繪。因為Julia Galloway的實用器物的創作靈感與主要影響根源於歐洲華麗的骨灰瓷,因此,她首次真正勇敢的來面對器物的形式以外的另一重要語彙。在萬事起頭難的狀態下,Julia Galloway無法滿意初期的成果,但在此因禍得福的機緣下,她的創作尤其是在表面處理達到了純熟與風格強烈的狀態。畢業後在Archi Bray藝術村的駐村時期持續創作,更讓她成為90年代末在美國最受矚目的一位實用陶藝創作者。
觀看徐永旭此時的創作,不由自主的讓我想起Julia Galloway,永旭過去十多年的旺盛創作力,是台灣專業創作中少有的,他除了在技巧上早已有長足的突破以外,作品主要以人體在主觀的抽象化過程中,企圖轉換對人性與當下社會文明的一種批判,此一風格正持續了近十年的時間。
在2003年進入台南藝術大學初期,永旭實踐了他當時決定回到學校的承諾,從零開始,面對自我對藝術追求的純原點“作者與作品”。當既有社會批判不存在的時候,就只剩下自己與自己的作品的對話了,有如Julia Galloway在斷手之後的羽化,我看到了永旭調焦的過程,抽象雖然仍是他表現的形式,但隱藏在物像以外的能量已更被純化。
他的作品由華麗狂野轉化成安靜與自省,讓觀者猶如進入了他建構而成的個人冥想世界,即使每個人存在著對永旭作品解讀與詮釋的自由,但仍逃離不了他作品散發的震頻。
當代藝術的發展,不只在傳達觀念的手段與方法多樣,媒材的角色扮演也早已被重新定位,單一媒材的創作早已被打入冷宮,被視為落伍,不具時代性的執著。從創作者的角度來看,挑戰自我、挑戰傳統、挑戰現代,則是建構藝術史演化的狀態,永旭的藝術創作和他對自我的挑戰在多樣紛亂的台灣現代藝術中應更難能可貴,因為在過多和追求形式現代化與媒材多樣化聲音中,還能像90年代末的”捍圖社”藝術家們那樣地作陶著並不多見,也因為對媒材的可能性,仍有著一份真誠,即使是固執,但這些微弱的聲音,絕對是維持台灣現代藝術能更多樣化和尊重多種創作發展可能性最重要的力量。
永旭這時期的創作中實驗性更強,這時的實驗動機則是在尋求自我與現代對話的最佳狀態,同時亦是建立自我認知的另一種方式,我期待更多的反動更強的顛覆更絕對的革命,在徐永旭的創作裡,
(本文作者台南藝術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