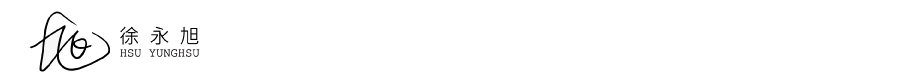脫胎、煉化_徐永旭的身與陶
前言
「形體為灰土,狀若明窗塵。」_《參同契》[1];「及乎脫胎,則形體閃爍,如明窗日影射塵之狀」_宋 陳顯微
在南部生活期間南藝校園內,除了自然的天光草色外,最令我記憶深刻的景象或許是一陣”夕瀑雨”[2]過後,午後陽光斜斜地灑在錯落於陶瓷組前方草地上,那兀自沾染著幾滴清透的雨露玄黑的薄胎陶作。這件大而蜿蜒、內斂的作品在南藝的這片草地上已然多年,隨著時間嫩綠的青苔甚至漂染在作品玄黑的表面,襯上作品內部的幾抹氤紅,彷彿時間與大地竟伴隨著創作者,為這作品注入了呼吸與生命。
這件作品是藝術家徐永旭在南藝修業時的作品,從這件作品開始,徐永旭的摶土煉化開始逾越那傳統上「現代陶藝創作」與「當代藝術」之間那道無形卻又難以逾越的鴻溝。靠著身體的勞動實踐,藝術家的創作走入了當代藝術中那針對美學、精神的探問與辯證中。而徐永旭的藝術實踐也猶如草地上那件透過徐永旭雙手漸次煉化陶土,在脫胎自生後與環境靜靜地融為一體的作品一般,徐永旭的藝術實踐也兀自獨立、自外於”陶”與”藝”的材料、技術的思維窠臼之外,走進了”哲學美學”的跨越及思辨中。
從南藝草地這件沾染著嫩綠苔蘚及清透雨露的作品開始,徐永旭的作品總是在靜謐中傳遞著某種生命的氣息,若緩緩呼吸的有機體般,自顧自地存在與衍生。在藝術家的作品形態中,無論是那宛若木耳般的小型體在層層疊疊間漫延出生長的訊息,又或者是層層迴轉宛若地脈流轉的大型體,作品那滿盈的動感與生命力的造型中蘊含著藝術家的身體運動軌跡、生命記憶乃至於每一次煉土化形時的情緒點滴。
儘管藝術家所追求的並非古老道家,玄秘煉丹的脫胎升仙之術,然而作品的型態與肌理卻每每精微地體現了”脫胎”時那流動幻變的精神形體。正是那面貌多變卻又型態統一的作品,讓我們在藝術家不同的作品中,都同樣地感受到”氣息”與”生命”與此同時也在多變的面貌中見證了藝術家其藝術精神的持續超脫與身體運動的越出。
每一次的創作,都是徐永旭自身與材料並進的脫胎與煉化,藝術家的作品脫胎於其身;而其身又復返煉化於作品之中,而徐永旭的藝術之道正在於在持續反覆的摶土煉化中,超脫與越出那已然成形的過往,脫胎而成當下之姿態。
- 弦外音_摶土的韻律
“錦箏彈盡鴛鴦曲,都在秋風十四弦”¬__顧瑛《玉山璞稿•斯歌二首》
「…人生總是充滿轉折與驚奇…」這樣的句法與描述,常常會在人物傳記類型的文學作品中看見,透過這樣的句法我們讀到了主角不同於尋常的人生,也看見了在人生轉折處主角的選擇與多數人的差異。同樣的這個句法用在藝術家徐永旭身上,不僅十分合襯,也同樣地將其充滿戲劇張力的藝術人生轉折給凸顯了出來。
早在開始從事陶藝創作以前,徐永旭的藝術人生便已經開始了,年輕時的徐永旭是知名的古箏老師,甚至在台北實踐堂開過演奏會,而台灣各地與徐永旭學古箏的子弟更是難以勝數。或許是這難得的音樂修為,讓藝術家十分傾情於韻律及躍動的型態掌握,從94年《舞蹈》系列的作品中,我們即可看見藝術家對於掌握生命脈動的鍾情與探尋。
音樂的教養及彈箏的訓練,除了讓徐永旭的作品中始終蘊含著深刻而鮮明的律動感之外,或許更為深層的身體感還投射在作品的表面肌理上,多年以後那撥弦、按弦時,各種「搖指」的手指動作,將在無形間轉化成藝術家自我脫胎之後作品表面留下深深的肌理印記,那些指尖按壓出的肌理與線條不僅記錄著藝術家的身體律動及姿態,更猶如按壓琴弦時所發出的各種聲響有著藝術家的感情、心緒與記憶。從記憶深處到逐漸浮現於作品表面,徐永旭那封存在歲月裡玩音弄樂的身體技術又走過了許多年月,直至2008年藝術家的系列作品,身體、韻律與作品形態,才終於合譜成為陶土上的名曲。
從撥弦的音樂家到摶土的陶藝家,徐永旭的藝術生命轉折充滿著機遇與巧合,當藝術家開始體認到古箏在音樂上的極限時,同樣身為小學教師的同事邀請徐永旭一起開設陶藝工作室,而徐永旭沒有多想就這麼投入了自己從未體驗過的新世界中。儘管是從零開始漸次摸索,儘管是陶藝世界裡的初生之犢,徐永旭卻在朋友離開工作室之後繼續走下去,而這突如其來的人生弦外音,竟悄悄地從生命的副節奏,慢慢地演變成徐永旭生命的主旋律。彈盡了鴛鴦曲的音樂家,在陶土上找到了自我藝術生命的弦外音,箏弦之外徐永旭的藝術旋律愈見悠遠綿長。
- 介係詞_在主流邏輯之外
“不只在語言中思考,而且沿著語言的方向思考”_海德格
如果說,從音樂走進陶藝是徐永旭生命裡傳奇的弦外音,那麼全身全心的投入便是藝術家堅決意志的展現,然而有趣的是或許正是因為這條陶藝之路,完全是徐永旭自我摸索的過程,也因此他走過了許多人沒有走過的路徑,學了許多科班出身者沒有學過的技術,也讀了許多陶藝專業人士可能忽略的重要相關知識,從而締造了徐永旭在與”陶藝”相關的知識上,有著寬廣而深刻的認識,然而這一切卻是從文字閱讀障礙開始的際遇。
一如海德格所言,我們的思考存在於在語言之中也順著語言的方向思考,然而如果不認識那個語言及文字呢?是否思考雨勢也將因而解放? 有別於其他科班出身的陶藝工作者,徐永旭以佛家語來說是個全然的「外道」,這讓藝術家的起步充滿了困頓,卻也給了徐永旭難以想像的自由與資產。受限於自身對於陶藝知識的淺薄與匱乏,徐永旭在決心走向陶藝以後開始了蒐羅書籍閱讀的歷程,任何書籍只要有陶藝作品及窯爐的照片,無論是以哪種語言印行出版的書籍,徐永旭絕不放過任何漏網之書,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徐永旭的英文障礙替藝術家帶來了意外的收穫。
藝術家曾經說過:「我的英文很差,連介係詞都看不懂….。」,這個連介系詞都查字典的藝術家也因此讀得比任何人都深、都久;更重要的是誤買的書給予了徐永旭在未來創作上難以估量的資產,從窯爐的整體設計到釉藥的化學原理及配置…等等,這些外於陶藝創作卻又相關的工程、技術知識,讓徐永旭在日後具備了自主設計、規劃、建造設備的能力,也讓藝術家一如化學家般得以自在的調配釉藥。而正是在這自我養成知識的背景下,讓徐永旭在相關陶藝創作的技術、材料以及工具方面的知識及實踐能力,具備了令人難以望其項背的功力。正是在這種絕對的技術能力上,讓藝術家的創作在90年代後期及至2005年這段時間裡,極盡能事的展現著造型、燒製及配色技術上的高度掌控能力,無論是98、99年轉化了亨利摩爾、布朗庫西的抽象人體交纏的作品「掔」,抑或者05年那褪去造型的繁複,留下顏色燒製難度的05年系列作品,都在在地顯現了徐永旭個人精湛的技術修養,更遑論如今藝術家工作室裡那壯觀得令人咋舌的窯爐,以及規劃細膩的煉土機器,全都是徐永旭個人所設計的。正是這一段外於正統陶藝知識教養的修練過程,讓美學家龔卓軍在看過藝術家自行設計的工具後,讚嘆地說道:「…這根本像達文西….。」
如果說”陶藝”的領域中有著既定主詞邏輯的知識系統,那麼徐永旭的自我養成之路就是一個人的後現代抗爭,在自己的介系詞系統中尋找各種知識串連的可能,從而拓展了”陶”的可能性。逸脫於傳統的語言及陶藝知識之外,徐永旭從查字典認識介系詞開始,拓展了自身的陶藝技術、知識及思考,而這一切將累積成藝術家從”陶藝家”脫胎成”藝術家”的資產,而其作品也將從”陶藝”躍升為”藝術”。
- 凝神成軀
“我們不僅僅思索我們的身體的各個部分的關係,視覺的身體和觸覺的身體的相關:我們自己就是把這些胳膊和這些腿維繫在一起的人,能看到它們和觸摸它們的人。用萊布尼茨的話來說,身體就是其變化的‘有效規律’”。─ Maurice Merleau-Ponty (莫理斯•梅洛•龐帝)
如果仔細觀察徐永旭歷年來的作品,可以發現各類型的「人體」在其早期的作品中,始終佔據著重要而鮮明的比例,從94、95年的「舞」系列作品開始乃至於2004年的「神話」,儘管造型不同且風格多變,然而「身體」卻始終是藝術家其藝術創作中,長期關注與發展的課題。而「身體」在徐永旭作品上的表現性與方式,則提供了我們深入凝望與體會藝術家其藝術生命歷程的參照。
如果說94、95年的「舞」系列作品,乃是藝術家針對「人體」關注的初步嘗試,則其作品中的律動感以及命名(舞),無疑地讓我們看見了徐永旭對於「音樂性」如何作為一種「人體」造型詮釋的探問與思索,與此同時藝術家在作品中所追求的尚有造型技術性的持續超越,這種對於技術超越的追求可以從96’97年的作品中看見端倪,而從97年開始徐永旭的陶塑與燒製技術的超越性,讓藝術家得以僅僅透過單一陶土線條的交錯、纏繞即可轉化為某種人體的姿態。值得注意的是,從96年以後徐永旭的「人體」除了在造型技術上的超越之外,更有著對整體藝術歷史的關注在內,諸98年的作品「容」便有著類似亨利摩爾其雕塑人像的氣質,而99年的作品「越」則有著布朗庫西的氣質,乃至於99年的作品「眺」等則有著原始部落人體雕塑的氣質,在這些高度技術表現性的作品中,我們看見了徐永旭在技術性與藝術史上的成長與發展,也看見了藝術家的視野從材料、造型的技術知識中跨越出來,朝向對藝術歷史的凝望與思索。
相較於99年以前的「人體」作品,徐永旭在千禧年的作品中透過「人體」更進一步地探討了立體及雕塑造形的基礎問題_尺度。在2000年那些大尺度的人體陶作諸如「如皇」等作品中,我們看見了藝術家不再一味地追求形體的多變與風格的嘗試,轉而以原始民族雕塑等更簡潔的造型方式來探索立體作品在「尺度」上的所帶來的感受性差異,而正是在這個嘗試及轉變上,徐永旭的藝術實踐及思索,開始從造型技術的實踐轉變成造型歷史的實踐;再轉變成造型感受的實踐,也正是在新世紀的初始,徐永旭開始了走出”陶藝”的藝術實踐之路。
從2004年開始,徐永旭的作品開始出現了大面積薄胎所摺疊或捲曲出的造型,諸如作品「神話2004-7」及作品「2004-11」等,在這些作品中身體的形象性開始消融、遞減,但同時藝術家的身體勞作卻更為緻密、龐大。在這裡藝術家讓我們看見了更深一層的藝術實踐與思索,如果說90年代的藝術家其藝術實踐的關注是如何創作身體造型(型態嘗試與塑造),那麼千禧年時徐永旭則關注於如何創造身體感受(尺度與環境),而04年以後的藝術家則更進一步的關注於如何讓身體感受成為作品。
如果說,2004年以後徐永旭開始將個人對「身體」的關注,從作品造型的問題轉化為作品創作的問題,那麼08年的系列作品正是藝術家個人的回應,在這系列作品中我們再找不到任何人體造型的擬仿與比喻,僅剩下無限衍生的作品自身而已,然而正是在這裡徐永旭的身體徹底的轉化為個人藝術的真命題,從而”陶土”與”陶藝”全成了藝術家在創作時的材料,甚至整個藝術歷史及過往美學的思索命題,全都在藝術家那「無器官的身體」_作品_熔冶一體。與此同時,藝術家的「身體」以及其藝術造型的「身體」乃至於藝術歷史及美學思索的「身體」命題,也全部匯聚在那展延、曲折卻又衍生的形態裡。
- 摶土煉化
“不是藝術應適應技術,而是技術的發展應適應文化及人文情境,這是當今所要求的”__P. Koslowski(科斯洛夫斯基)
藝術何時發生(When is Art?),從藝術歷史的角度上看這個問題,則偶發藝術(Happening Art)的誕生,機巧地回應了這個問題:「任何時刻,藝術都在發生」,然則這個看似無可置疑的答案,卻沒有告訴我們該如何得知藝術發生的時刻? 如果從觀察創作者的角度,再次探問:「如何得知藝術發生的時刻?」那麼我們或許可以說當一個創作者意識並實踐了科斯洛夫斯基所說的:「技術的發展應適應文化及人文情境」時,藝術便發生了。
從「技術的發展應適應文化及人文情境」這個角度上看徐永旭一生的藝術實踐,則我們可以清楚的發現,藝術家真正擺脫”陶土”的材料限制、”陶藝”的技術、歷史限制發生於2004年以後,然而實踐上的完成則到了08年才真正的擺脫了”陶藝”作為一門”技術”的窠臼。也正是在從08年以後徐永旭得以真正的宣稱其個人的創作實踐乃是從身體出發的美學辯證。
仔細觀察藝術家自08年以來的創作,可以發現其基本上從兩種基本的型態元素出發,而漸次發展成三種到四種基本的型態元素,這些基本型態元素在08年的系列中我們可以看見主要是已如貝殼、木耳造型般的小型單體,進行宛若生物蔓生、繁衍所堆疊出的造型諸如作品「2009-2」,以及細薄大平面仔展延、曲折所構成的大體積型態諸如作品「2011-16」。而這兩種基本型態元素又時而結合、交錯形成另一種型態的作品如作品「2011-18」等。若不經意思索與凝視,徐永旭一系列些從基本型態元素衍生而來的作品乍看之下很難分辨出其差異,然則所仔細凝視與觀察則可以發現藝術家其作品衍繹的精微之處。
從傳統的角度上看,摶土乃是擠壓泥土分子間的空間使其成為緻密的一體,而煉化則是將摶好的陶土進行立體型態的自由表現,然則有別於傳統陶藝安定的保持著3度空間的立體性格,抑或嘗試復返2度空間作為陶畫的平穩手法,徐永旭的作品其精微之處正在於藝術家透過身體的每一個細微做工,所累積出的不僅是細膩的單體元素,更重要的是在層層疊疊、反覆交錯間所構成的碎形維度變化,如果說波洛克(Jackson Pollock)行動繪畫打破了一維線條與二維平面間的關係,成為了游移在一度與二度空間的身體律動紀錄,那麼徐永旭的作品則是游移在二度與三度空間的身體演奏軌跡。正因為藝術家打破了平面與立體之間的絕對性關係創造出作品型態碎形的維度,以及如細胞分裂般的單體元素重複性衍生,從而讓我們總是能感受到作品自身的生命力量。
然而徐永旭更為深刻的藝術突穿,或許是打開了”陶藝”其摶土與煉化的閉塞眾竅,觀察其藝術的實踐過程,可以發現藝術家真正摶煉的並非是陶土而毋寧是在看似摶土的反覆搓揉中琢磨出深具生命力的基本型態元素,而其煉化的乃是身體種種觀感、認知如何融入、佈排那被細細琢磨出的基本型態元素,也因此在徐永旭的實踐中,摶土成為了身體姿態的凝聚,而煉化則是美學思維的展現。
- 脫胎
“事實上,我們不會看到一個精神能夠繪畫。畫家其實是把自己的身體放進世界,才能把世界轉變為繪畫。為了理解這種身體移轉,我們應該要重新找回正在活動中的真實身體,這種身體並不是一塊空間的碎片,也不是一堆功能的組合,而是視覺與運動的一種交織狀態。”─ Maurice Merleau-Ponty (莫理斯•梅洛•龐帝)
儘管引言中梅洛•龐帝所描述的畫家與繪畫的關係,然則事實上其所真正提出的乃是藝術之所以成立的核心理由。從哲學家的描述中可以發現,真正的藝術始終是脫胎於創作者的精神與血肉的完整身體。從這個角度上看徐永旭的藝術實踐與歷程,可以發現從2008年以後正恰恰呼應了哲學家的看法,然而或許更為重要的是藝術家究竟為藝術的發展帶來了甚麼? 如果徐永旭僅僅實踐了過往美學的理想,如果徐永旭的自我技術僅僅是完成了過往藝術家的實踐,那麼其藝術又如何脫胎呢?
當我們從當代藝術的角度上重新檢視徐永旭的作品以及其與“陶藝”、”陶土”及”身體”的關係時,可以發現相較於傳統”陶藝”從”陶土”此材料開始思考”造型”的問題,並以造型表現作為創作的終點,徐永旭的實踐則是從”陶藝”作為材料開始思考”身體”的美學問題,並從”身體”回返至”陶土”進行表現,而其特意固執的選擇一門歷經萬年歷史的”技藝”作為其藝術實踐工具的姿態,則清晰的體現了居伊•德波(Guy-Ernest Debord)提及當代藝術創作時,認為一個當代的藝術家其真正的力量來自於”態度”。透過”陶”一方面徐永旭挑戰著”陶藝”古老的歷史,另一方面也挑戰著何謂”當代”的藝術? 而正是這個二元性的挑戰態度,讓徐永旭的作品脫胎而成當代之姿。
[1]《周易參同契》又名《參同契》,是關於煉丹術的著作,被稱為「萬古丹經王」。作者是東漢的魏伯陽。《周易參同契》的書名中「參」為「三」,指周易、黃老、爐火三事。
[2]台語“夕瀑雨”即一般因諧音而誤稱”西北雨”的午後雷陣雨。其原意為午後(夕)如瀑布般(瀑)的滂沱大雨,正字原意甚優雅而具詩意,因此特地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