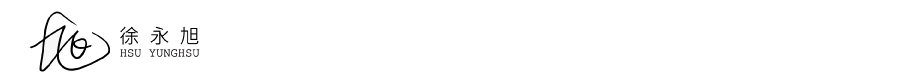身‧形-談徐永旭作品中的「自在形」
我是單純的沒有思考的生物?我絕對不是,我一定有思想、我有學院的訓練,但是我在做的時候我希望我沒有思想,我就像生物在織網一樣,我的作品就在處理這之間的問題。[1]
— 徐永旭
「身」與「形」,是徐永旭作品 看似簡單重複的作品創作裡,重要的兩大元素,經由不斷重複與土來回互動的身體,形被產生。但作品的形,在他的創作中並非創作一開始的設定,亦非真正的重點。徐永旭強調: 「在我創作的當下,造形並不是我的重點。我作品中的『形』是在不斷重複的身體動作中,透過最簡潔的土的形態結構需求所形成的。」[2]他像吐絲的蠶、建構蜂巢的蜜蜂或是結網的蜘蛛般,以貼近生物的身體與土的互動,創作過程中幾近無意識地重複乃至成形。這也就是何以他的作品總是帶有著自然而然的生物氣息,宛若自然之物。徐永旭的作品形態來自於對於解放存在於身體的既存知識與教育訓練,藉由他所謂的「去」的動作,讓身體自在,以自由地成形。換句話說,徐永旭的創作重點並不是在通過藝術家創作意識所形構的「形」,而是企圖藉由徐永旭身體與土之間的來回接觸過程,呈現他的身體與土關係或是與自然關係的「自在形」。而這樣在創作過程中雖身體辛勞,但心靈卻是自在的,自由自在的身體是貫穿他創作的嚮往。
返元
返元的概念在徐永旭的創作裡,是最基本的,也是貫穿他整個創作的根本,所以他的創作是將身體返元,同時也將創作返元。他在2014的展覽名中所稱的「元行」(prototype),也就是這樣的概念出發,從作品來看,呈現最單純、自然的特性,也就是回歸到最原初的人與土間、人與自然的間的關係。
徐永旭的作品所操作的就是一些基本元,也就是身體的重複與土本身的特性這兩個最基本的元素,在成形過程中所有的工具只有一條切土的鐵線。在談到他創作的過程他表示:「形式語彙,在我作品中我都盡量讓它很回歸到簡單的動作跟語彙型態,所以在我創作成型過程中,我所有的工具就這條鐵線,用來把整個土切扁,就這樣,完全沒有任何工具,就這一雙手跟泥土來處理這個概念。」[3]也就是說,在他的創作過程中,他希望呈現他的身體跟土之間的單純互動關係,藉由這樣幾近無主體意識的重複動作,以貼近最生物性的身體建構屬於由他,徐永旭身體與土相互消融滲透所產生土的形體樣貌,這就是他作品中形的產生的過程。工具的發明是知識的累積,因此捨棄工具的原因在於他企圖在創作過程中儘可能的將理性與知識的去除,讓身體得以直接與土面對,這就是他所謂「就這一雙手跟泥土」所要表達的概念。
他將創作返回陶土與身體最原初的狀態,以泥土最基本的土團製作捏製與土條接合,不斷重複,小體積的在指間成形不斷積疊,體積大的就以土條成形運動全身。在視覺上,徐永旭的作品可分為三個主要的作品形體基本元:單一如對切的蠶繭抑或海洋裡的蚵殼,略為展開時也像是錦簇的花叢或茂密的葉子造形;其二宛若海帶般循環交纏的造形;另外,還有大面積片狀流轉穿透的作品造形。這三種系列的作品,體現了徐永旭最元初的身體律動所構成的造形,而這些造形的存在也依賴著作品所需的力學結構而存在,這展現了徐永旭自然身體在指間、掌間、與身體間不同身體尺幅下,生物身體所處自然環境空間元素隨作品最基本元的結構功能,形成的諸種「自在形」。
重覆
重覆的視覺形式給人秩序性、單純及規律的感受。這也是徐永旭作品造形雖然是不定的有機型體,但卻帶給觀者極簡造型的感受。事實上,在甫觀看徐永旭的作品時,觀者一開始觀看到的是有某種超高相似性的重覆模式(pattern),這樣的視覺景觀是有秩序的、簡潔的,帶給觀者平穩而寧靜的跟隨。他表示他的創作就像蜘蛛織網「就是我每天在那邊一直織一直織嘛,這些語彙就這樣這麼簡單的,然後我所有的創作就是這個樣子。」[4]但這樣的重覆在靜距離觀看下,難不感受到他作品中不斷重複的是大量身體的痕跡,這樣的痕跡在了解那是徐永旭的身體痕跡後經常的給大部分的觀者一種身體過勞的衝擊。但對徐永旭而言這樣不斷的重覆,卻是一種心靈的解放。就我而言,從他作品指印所留下規律的頻率痕跡,讓我聯想到木魚的韻律。木魚的功能在於讓誦經之人將心傍於木魚的節奏上,攝心而不落入自己的昏沈及分想當中。也就說是規律的節奏可以使人在跟隨節奏的過程中,解放身體而進入一種專注的冥想。就像是人的心跳頻率,當情緒高張時頻率呈現著激烈的波動,而心理平靜時,心臟變會呈現穩定而規律的頻率。
另外,看似重覆的造形呈現了歷時的多樣性身體,也同時的表現共時性的普遍性。亦即徐永旭作品中的重覆,不但表現了他的身體在不同自然變數下個別差異性,但相同的製作過程卻也體現了大自然的普遍規律性。而這兩者便是重覆的因素,使觀者在觀看徐永旭作品時,同時覺得每件作品存在著差異,但同時卻又具有共同調性的原因。
自然而然的造形
既然徐永旭企圖以「去」的方式來創作,但是他作品中造形究竟從何而來?關於造形的形成的形成,或許我們可以援用路易士‧蘇利文((Louis Henri Sullivan,1856-1924) 的「形隨機能」(form ever follows function)[5]的功能美學的角度來觀看徐永旭作品的造形。所謂的「形隨機能」的概念,也就是形式總是跟隨著功能而存在,對蘇立文來說,功能形成造形這是不變的法則,他指出功能不變,形式也不會改變。以此角度,便可觀看藝術家作品中身體存在的軌跡。同時,蘇立文的美學也是自然主義的,他認為功能美學可以從飛翔的老鷹及蜜蜂的蜂窩等大自然中獲得印證,這些大自然生物的美感形式都來自於其生存的需求功能。這些生存上的需求,是自然而然的演化而來,是符應功能的需求而形成的形式樣貌。在談到他的作品創作時也與蘇立文有不謀而合的觀點,他說:「其實我在做作品的感覺像是在織網,我的身體在像是比較本能的,像是動物性的,生物築巢的本能。」[6]這樣的功能性美學便是為他的作品提供了重覆相似形的根本來源,亦即,基於作品的結構強度功能需求,於是徐永旭的創作便呈現了某種接近的重覆性。但是,這樣的重覆性在解放身體、環境與材料的變數下,呈現了重覆之外的個別性,進而呈現了自然而然的造形樣貌。
返回單純身體的自在形
在徐永旭的創作中,創作意識的主體,也就是徐永旭,在作品中,存在著,也不存在。這看似矛盾的句子,事實上,包涵了徐永旭創作的功能美學及自然美學。存在的意思是,在他整個創作的過程中,他企圖丟棄身體中被建構的理性甚至是感性的輸出。在談到身體在創作過程中的時候他表示:
我很希望在創作的時候我是生物,把自己完全是不去思考、不去做什麼,甚至是沒有指使的,只是一個肢體在這裡處理一個東西。我是有一點朝這樣在思考,但是當你這樣的時候,你很刻意要,如果我們用比較理論的話來講,就是說:我想去知識化,當你要『去』,事實上你去掉了你這個『去』本身就是一種指使,但是我有想要『去』,這就在那邊拉扯,事實上這一些作品就是在這樣拉扯的狀態產生出來的東西。[7]
也就是說存在著的,就是在維持最原始結構造形的徐永旭,他以不斷印壓的指印,雙手的印記及主體身體的尺幅存在於作品之中,也就是他所稱的作品「…就是從我身上拿出來的,這個材料就記錄了跟我那段時間的相處…」[8]。另外,不存在的意思也就是說,在作品創作過程中,身為創作的主體的他,並沒有刻意設定某些造形,而是跟隨著與土重覆接觸的過程中作品成形,以自由的身體狀態創造作品的「自在形」。所謂自在便是「自在是不受影響,不考慮自己的得失、利害。」[9]這當中,所謂的「不受影響」,應是身體所受的知識建構,抑或是情感波動,以不受阻礙的心觀看世界,便是自在。從企圖解離的創作主體的狀態看來,「自在形」是徐永旭藉由掏空自我的身體,讓自然自由自在地充盈,呈現著徐永旭、造形與自然相互融合著的造形。這也就是簡子傑所稱徐永旭的作品:「浮現出一股身體與媒介之間相互交滲的不確定狀態」[10]這樣的狀態就簡子傑而言是「…『藝術家—身體—陶土』形成的是一組異質同構的連動軸線,它們相互流變為彼此,藝術成為生命形式…」[11]就是說,徐永旭的每個當下身體與材料相互滲透,合而為一成為彼此。
徐永旭的作品並非以理性的方式「師法」自然,也就是他的創作並非模仿或再現自然界中的造形,而是「承自」自然。他以「去」的方式企圖將身體主體意識解離,虛空社會身體以承自然。「我做作品是另外一種狀態,如果做大件的時候那狀態像是起乩,那是在跟我的身體跟環境、跟這個材料在搏鬥,」[12]他所謂的「起乩」也就是他虛空了主體的意識,讓自然在他不斷重覆的過程中導入他的作品中。這也就是龔卓軍所稱,徐永旭身體與環境、材料等的「混沌互滲」「…諸如氣候與微氣候的環境與材質互滲問題,這些「混沌互滲」的過程,涉及了作品的時間性與材質的變化,包括空氣溼度、泥土的物質性、風、壓力、氣壓,空間狀態」[13]這些環境與材料的變因,被導入到徐永旭虛空以待的身體,藉由身體的開放,憑藉功能美學的回返,呈現自然而然的「自在形」。
[1]摘自2017/02/21與徐永旭訪談。
[2]同上註。
[3]同上註。
[4]摘自2017/02/21與徐永旭訪談。
[5]Sullivan, Louis H. (1896). “The Tall Office Building Artistically Considered". Lippincott’s Magazine (March 1896): p408.
[6]摘自2017/02/21與徐永旭訪談。
[7]摘自2017/02/21與徐永旭訪談。
[8]摘自2017/02/21與徐永旭訪談。
[9]聖嚴法師著,《心的經典 : 心經新釋》,新北市:法鼓文化,1997。
[10]簡子傑著,〈關於如何從一成為多:寫於徐永旭2015年個展「Helios旭HiOK」前〉。 於徐永旭著,《Helios旭HiOK》,臺北市:双方藝廊,2015。
[11]同上註。
[12]摘自2017/02/21與徐永旭訪談。
[13]龔卓軍著,〈逾越與混沌滲透的美學辯證:論「突穿眾竅:徐永旭1992-2014」展〉,《突穿眾竅:徐永旭1992-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