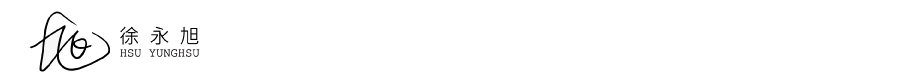大器逍遙:徐永旭個展
1. 肉身造型
徐永旭的藝術創作既是造型的藝術,也是思想的藝術,更是生命實踐的藝術。從他開始從事藝術創作以來,他持續不斷琢磨自己與泥土之間共生的厚度與對話的深度。自1990年代逐漸嶄露頭角,歷經三十年的努力,他已經建立了自己的獨特風格,如今已經獲得國際的聲譽,更為這項藝術注入了豐富多重的結構與造型,拓寬了空前壯闊的視野。
1955年,徐永旭出生於臺灣高雄,1975年從屏東師範畢業之後,曾經任教於小學,並且也曾經是一位知名的古箏音樂家。但是,他在1987年開始成立陶藝工作室,1992年師事陶藝家楊文霓,1998年毅然放棄已有22年資歷的教職,也放棄了已有成就的音樂生涯,決心以創作做為終生的職志。2007年,又在張清淵的指導之下獲得國立臺南藝術大學碩士學位。
帶著旺盛的創造力,徐永旭很快就進入專業的藝術舞臺。從1992年,他逐漸建立自己藝術的初期風格,並且受到國際矚目,不但經常獲邀參與國際展覽,也得到國際陶藝專業期刊專題報導與評論。
從1992年到2012年,徐永旭的藝術創作已經展現出豐富的造型特色與美學意涵,呈現出清晰可辨的演變軌跡。如今,我們可以將他的創作歷程整理出五個時期[1]:
第一,生機主義時期(1992-1997):這個時期的主題是「戲劇人生」,主要包含兩個類型的作品,第一類是以單一造型元素發展出來的初期作品,第二類是以舞蹈姿勢為造型並帶有音樂性的系列作品。
第二:超現實主義時期(1997-2004):這個風格,主要出現在他取名為「位」的系列作品中。這一時期作品,一如超現實主義的傳統,雖然表面看似幽默逗趣,其實卻是充滿著隱喻性的社會意涵。
第三,抽象表現主義時期(2004-2005):這個風格,出現在「神話」系列作品以及看似碎片或局部的簡單造型作品之中。雖然這是一個短暫的階段,而且作品數量極少,但這是他從具象轉變到非具象的重要時刻。
第四,過程藝術時期(2005-2012):這一時期,以裝置藝術方式呈現,而在創作過程之中卻又隱含著觀念藝術與行為藝術的元素。2007年「黏土劇場」系列作品,都是他以黏土為材料經過窯燒完成的「極大極薄」的造型作品;依照他自己的解釋,這些都是他為了逾越自己身體的極限而創作出來的作品。
第五,形上美學時期(2012- ):這時他既延續昔日「黏土劇場」的創作脈絡,卻也同時開始轉變,一方面他在黏土劇場的大型結構之中增添為數眾多的小型造型元素,發展出類似於集合藝術的結構,另一方面他也單獨使用這些小型造型元素,以堆疊或並列的方式,延伸擴展為巨大壯觀的造型。
2. 逾越疆界
從2012年以來,徐永旭的藝術創作再次進入一個自我突破的旅程。這一時期的作品,既是造型藝術的形狀與結構的改變,也是關於藝術作品的美學向度的重新定義。
從材料方面來看,他務必進行土材軟硬程度的精密檢測,而同時他也務必針對小型造型元素之間結合的穩定程度建立捏塑與燒製過程的技法。過去,巨型劇場造型必須克服捏塑過程的坍塌與燒製過程的龜裂,如今,則是必須避免小型元素之間的擠壓與脫落,充滿更多無法完全預測的創作風險。但是,徐永旭卻能夠運用高度科學的能力,自己設計創作與移動的巨型載具,再透過創作活動的直覺能力,讓這些作品可以逐一順利誕生。
從結構與造型方面來看,它的體積無論是大是小,都呈現出高度複雜的結構,也使得作品呈現出從結構的組織性延伸而發展出來的造型。這些造型,有的立體站立於三度空間之中,既是雕塑,也是裝置,有的可以懸掛於二度的牆面卻因為尺寸可觀的厚度,而增加了多重維度的視覺空間。
這一時期的作品,徐永旭從「過程藝術」轉變到另一個藝術思維。2012年以前,在「黏土劇場」系列作品中,我們看到的是以土條的綿延伸展銜接建構起來的巨大造型,而在創作過程中,他的身體跟隨著巨大造型的結構進行伸展的活動,彷彿他的身體已經隨著土材進入造型之中,似乎造型與身體已經相互交織,流動著相同的血緣。至於2012年以後的作品,創作的工序卻是首先捏塑一個個的小型造型元素,然後逐一並列擴張面積並且逐層堆疊,形成類似集合藝術的巨大造型;這時的工作顯然從小結構出發,建立大結構,而身體活動則是從小範圍朝向大範圍移動,直到完成巨大造型。固然也是延續著過程藝術的精神,但作品的尺寸規模與身體活動範圍,卻是更為自由活潑。
如果說「行動繪畫」(action painting)[2]一詞可以用來形容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繪畫活動的身體運動,那麼「行動藝術」一詞應該也適用於詮釋徐永旭創作的身體運動與姿勢。在徐永旭這項行動藝術的創作中,他明顯地使用了兩種造型元素:一個是如同貝殼的造型元素,另一個則是帶狀造型元素。
首先,如同貝殼的小型造型元素,就像是擀好的水餃皮做出凹陷形狀。有時像是花生殼,有時像是蚵仔殼,也有時像是脫落的稻米外殼。但事實上,它們並不是這些東西的象徵物,它們只是他用來建構巨大造型的物體單位,讓作品產生結構,一方面產生量體的物理層次,另一方面也產生虛實、明暗與高低起伏的視覺層次。其次,帶狀的造型元素,則又像是手工麵條,也像是更大尺寸的昆布或海草,但事實上,它們也不是這些物體的象徵物,它們是用來改造空間方位的運動元素,也就是說,它們是讓靜止發生運動並發生時間的線條元素。
然而,這次徐永旭的藝術創作的演變,基本上並非只是造型形式與視覺美學的演變,而是從哲學層面發生的美學思想的演變。他的藝術創作正在從身體疆界的探索朝向具有東方形上學精神的美學立場移動。
3. 大器逍遙
從徐永旭的創作歷程來看,從2004年的抽象表現主義時期以來,他的作品就已不是具象,也不是象徵,更不是器物。從2007年「黏土劇場」的作品以來,更是明顯呈現出過程藝術的精神,著重於探索身體的活動疆界,而這時的藝術創作也已進入思想層面,而不是停留在物質層面。
關於徐永旭創作思想的發展,我們可以引用《周易·繫辭上》第十二章所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一語,說明他正在表現一種奠基於東方形上學的美學思想。也就是說,他的藝術創作,並不是製造形下之器,而是探索形上之道。但東方與西方形上學存在著一個基本差異,西方形上學是一種從物理學具體現象找尋抽象原理的形上學,但是古代儒家與道家的形上學則是面對一個事物的兩種境界,從形下觀點去看便是器,從形上觀點去看便是道。所以,小器怎麼看都是形而下的器,而大器卻不等同於形而下的器,因為大器已經沒有形狀,沒有疆界,如同形上之道。這個觀點,《老子》第四十一章〈上士聞道〉也曾做出相同的詮釋:「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這段文字之中,「大器晚成」往往被錯誤解釋為建立成就的時間早晚,但事實上,依據前後文句脈絡,正解應該是大器無用,也就是說,大器不具實用的功能,也不是只供視覺的觀看,它是以器載道,並隱藏於沒有名稱的狀態之中。徐永旭目前這一時期的作品,往往沒有指涉意義的標題或名稱,或許也正呼應了「道隱無名」的觀點。
我們並不認為藝術家的創作活動可以完全引用哲學理論來詮釋,但是面對徐永旭的藝術創作,我們卻可以看到他從造型藝術延伸到思想藝術的演變,並且延伸成為生命實踐的藝術。因此,我們嘗試以「大器逍遙」來說明他的美學境界。
所謂「大器」,固然是因為生命實踐的深度與創作思維的高度,更是因為他的藝術創作已經表現出東方形上學的美學境界。所謂「大器逍遙」,則是因為他的藝術創作已經超越了現實世俗的觀點,展現出藝術家對於精神境界的嚮往。關於「逍遙」,《莊子》〈逍遙遊〉一篇曾經說過:「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這段話是說,大樹之大,或許無用,但是擺脫現實世俗觀點,放進沒有地理座標的天地之間,我們卻可以把它當做自由逍遙棲身的地方。
從大器逍遙的觀點,我們進一步也可以發現,徐永旭創作心靈的深處,從來不曾放棄音樂,只不過以前他的音樂是透過樂器傳給耳朵而屬於聽覺的音樂,但是從他致力於創作以來,他的音樂已經發生於他的身體的全部,每當他透過陶土發展結構與造型的時候,音樂便被鋪陳出來,這時音樂已經超越聽覺,也超越視覺,而是流淌在他的造型與世界共生的場域之中,表現為一種具有精神境界的形上音樂。這正是所謂「大音希聲」。
「大器逍遙」是徐永旭的藝術創作目前達到的深度與高度,這是一個朝向精神層面探索美學境界的藝術實踐,也是登高望遠的生命實踐。他開拓的不只是藝術的造型視野,也是當代藝術的精神向度。
[1]筆者曾經在2012年撰文將徐永旭的創作歷程整理出四個階段,但是經過這幾年,他的創作已經又朝向第五個時期。廖仁義,〈從卑微的塵土到壯闊的宇宙:徐永旭陶土造型的美學意涵〉,《周流·複歌:徐永旭個展》,臺北:耿畫廊,2012。
[2]這是指美國現代藝術家波洛克以站立的姿勢由上往下讓畫具的顏料自由滴落在畫布上形成的繪畫。這種作畫方式中,藝術家運用的不只是雙手作畫,而是全身作畫,因而繪畫是全身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