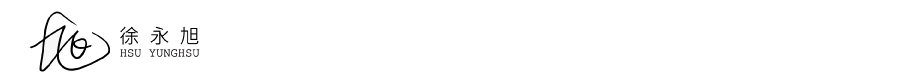反其道而形-看徐永旭藝術創作的「反陶」觀念
進到徐永旭的工作室參訪,巨大的空間中有著一種自律而緊繃的場域氛圍,這是他藝術的實驗天地,看著藝術家熟練的操作每一個器具開關和零件,憨直的笑容中總散發著不自主的焦慮,不時在臉上還透露出些許的疲憊感,他的身影孤單卻英氣勃發,隻身穿梭在龐大作品林立的空間裡面,這是他一個人的天地與王國,一個多年來獨自思索、面對挑戰並必須接受不斷失敗與成功的生命告解室。倉庫裡整齊排放的大量進口陶土,說明著一種隨時等候藝術家發號施令、開始工作而有的準備,兩個有著幾乎國際上個人工作室最大的陶窯也待命著面對藝術家給予的最大挑戰。
個性決定命運,觀念決定作品
徐永旭個人的素樸氣質,有著土壤的穩重、沉定,一種東方人特有的內斂平和,這可以直接投射在其作品散發出來的質感與氛圍,但其在個性上卻有著當代藝術家敢於挑戰、顛覆與創新的強悍與勇氣。當藝術家選擇以一種最困難與外人最難以理解的方式對應著他最熟悉的創作媒材時,即揭露出在他作品與身上可以看到的一種矛盾衝突,溫柔而霸氣、念舊卻反骨、東方且西方、熱情又安靜的揉合交融。也因此觀看徐永旭的作品時,有著強大的戲劇張力、節奏與層次感。
凝視著眼前的作品,忍不住會被那又大又薄的陶土量體震懾吸引,並步步產生疑惑。吸引的是陶的造形在藝術家以身體與之對應下創生出來的形式,有著與我們對於過往陶作認知完全相異而全新的視覺撼動,是一種當代陶作的新形式與路徑;疑惑的是藝術家採用了何種技法、工具與觀念,突破了陶土先天的媒材限制而可以隨心所欲的形隨意轉?於是一連串的驚歎號與問號就這樣從作品的巨型陣仗中不斷湧出。
面對鎮日與之為伍的陶土,徐永旭以反覆實驗與探索的方式為其創作的可能性鋪路,不斷地嘗試以手指按、壓、擠、撕、捏、點、磋、疊、推等方式解構陶土,也試著以身體和其他部位做為工具支撐、扶持、走動、環繞、等待,進入到作品的形塑與呈現之中。這樣以身體做為創作器具的概念可以印證到法國哲學家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1908-1961)知覺現象學裡的身體觀,藝術家的創作哲學摒棄了傳統哲學中,以「主體—客體」二分法的哲學論述,而是以「身體—主體」開展出來的,將一種我與身體融為一體的方式面對陶土,「以作為主體存有的『我』與作為物質肉身的『身體』,相互結合在一起,視為不可截然二分的全體結構」[1]。然而在這裡指出的身體並非如我們認知的物質肉身而已,也並非只是一個容易直觀理解的主體。這個身體藉由知覺、觸覺與痛覺,使「身體—主體」在現有以陶為主的結構之中和世界相互流動、作用並與之形構作品主體,使外在與我成為一種體現的世界,彼此融合,彰顯存有的意義,成為美學上的「物我為一」。這是徐永旭生命、美學與哲學的主要觀點,從此論點出發,進而引領觀者進入到目前所看到的他與作品。
反陶
因此,陶在他全心以身體試驗下的結果逐漸擺脫了原本厚重固執與尺寸的先天限制,將其「極大極薄化」後,反而有了一種輕盈的巨大量感,出現了令人嘆為觀止,在陶作中難見的「大」作品或「薄」作品,表現出陶既重且厚的另一面,一個陶藝史上從未有過的觀念與造形—極大極薄,以一種反其道而「形」的方式被創造出來,顧謂之「反陶」。在進入到2006年的創作階段時「反陶」觀念宣告成形,一個獨特而個人化十足的美學觀點,開始成為徐永旭創作的分水嶺,自此他將台灣陶藝創作帶入了另一個新的世紀、高度與風景,而陶也超越了陶的極限,成為其用來轉化其藝術觀念的材質,而他的創作則成了一種融合造型、行為表演與觀念的藝術創作。
在進行著「反陶」觀念的同時,面對陶土因為天候和溫濕度不同而無法掌握的現實條件與天性,徐永旭選擇的是把成功因素與可依賴的安全感給排除掉,迫使自己陷入到作品可能隨時崩塌毀壞的困境,藉由對身體的試煉進行著重複探索與行為演出,並企圖對於創作慣性進行著破壞而不停轉換尋找其他可能,但最後「換」本身竟也成了一種慣性,因此在種種確定與不確定的內外在因素包夾下,整個創作過程就充滿著變數與緊張狀態;在嘗試各種身體感之後,最後又循環到最初,而最開始的緊張也全然消失,取而代之的就是輕鬆,一種超越了界限的輕鬆,整個創作就這樣重覆著,身體的緊張感也就如影隨形、上上下下。而此時身體感成為「一個在內與外、過去與現在之間難以名狀的現象。因為,『身體感』不僅對應著外在對象時產生的動覺、觸覺與痛覺等知覺活動經驗,也涉及了身體在運行這些知覺活動時從身體內部產生的自體覺知迴路」[2];另外,這「『身體感』不僅來自過去經驗的積澱,它也帶領我們的感知運作,指向對於未來情境的投射、理解與行動。」[3]
徐永旭在這樣的狀態中不斷企圖再創難度,再次跨越界限,因此也就不停進入到另一種生命狀態與場域,用身體再去嘗試,直到進入一種重複循環,因為對藝術家而言,生命的本質就是重複,週而復始的生命迴圈,但藝術創作的態度卻是要求創新而不重複,所以徐永旭選擇了以『身體—主體』開展,在重覆之中尋找創新與解決之道,因此過程中的身體感也就藉由指紋或指壓轉化到陶作表面,形成不同的肌理,千百萬個的生命印記,其中所產生的身體痛楚與磨難則不斷被放大,整個創作行為也就被建立在一種臨界點之上,身體感強烈,而存在感也就相對地更為明顯。
大單元˙小單元
「反陶」觀念後的作品呈現大致上分為兩種表現,筆者稱之為「大單元」與「小單元」。「大單元」主要展出在2006年台南藝術大學的『界.逾越』以及2008年高美館的『黏土劇場』展覽中,作品以單一或成雙的群聚方式展現出來,看著一個個巨大的陶作陳設於其中,有著類似海底植物或巨石陣的神祕特質與宗教儀式,加上光影與空間虛實相映的對照,觀者彷彿走入中式情調的園林山水,與取法自然的奇岩怪石有著巧合相似的視覺語彙,既安靜卻又帶著強烈情感的氛圍,盈滿著精神性,就像許多表演者與觀者之間正進行著藝術的對話,讓現場有了劇場特質的詩性空間感。
大單元的陶土材質、低限語彙以及有機造型呈現的巨型量體,使人容易聯想到西方五、六零年代低限藝術(Minimalism)裡的視覺形式,但徐永旭作品裡的觀念與行為卻與低限藝術裡冷靜無情感的訴求以及對應於當時現代化議題的展現相異甚遠而無關聯,反而是一種凝鍊具有溫度的情感,是自成一格的藝術展現。
傅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曾指出人類運用四種包含「生產技術、符號系統技術、權力技術以及自我技術」的方式來認識自我,而其中的「自我技術」強調「個體用以影響他們自己身體、靈魂、思想和行為,以便能形成和轉化自己…反省地探討『自我、靈魂和心』」[4]之觀念,在此時期的徐永旭透過一連串身體探索與試煉將自身轉化為其藝術美學的追求;也就是說, 「自我技術」成了藝術家個人探究其美學核心價值的主要方法論,嘗試藉由追尋各種不同逾越界限的生命經驗與內觀認識自我。
進入到2009年的台中月臨畫廊『再』與2010年台北當代藝術館的『再‧之間』展覽,徐永旭的「反陶」觀念進入了「小單元」的系列,「小單元」不同於「大單元」的難以掌握,是藝術家在試驗當中偶然地發現了另一種身體感而逐漸發展出來的造形。一個個可掌握的小單元在形塑的過程中,依然有著身體的緊張感,只是那緊張感從顯性轉為隱性,身體的狀態也較為輕鬆,但在重複同樣的指法與動作,一個個小單位的堆疊下,作品自身產生的隱性緊張感,隨著外在環境的溫溼度與作品體積加重下的壓力,一直慢慢的浮現,越來越清楚而逐漸升高緊繃,如箭在弦上,其中牽引出的身體感則更為清楚的被體驗,彷彿是徐永旭將身體一片一片剝下堆疊而成,深刻感受到身體被置換過去,作品和身體則互為部分與主體,很貼切於德勒茲(Gilles Louis René Deleuze,1925-1995),認為的思想是在物質中移動流轉,沒有所謂心智和身體二分法的論點。
「小單元」時期創作的狀態確實與後來德勒茲提出的唯物觀點-「無器官身體」(body without organs)有所呼應,它不是一個完整以及具備靈魂的身體,它是一個無限延伸放大,超乎任何可以經驗的身體界限。它是斷裂也是接合,是組合同時也分解,「一個不連結的綜合,一個反生產的機器,不斷地瓦解、延宕、凍結、崩潰,因而分隔、中斷欲望機器迴路,但同時也將欲望機器多重、貫穿的迴路彼此連結。」[5];而藝術的生產,或者如德勒茲所陳述的欲望的生產都「是純粹的多重性,亦即絕對無法化約成整體」[6],過往稱之為「世界」、「自然」、「物質」的說法在德勒茲看來都可以被稱為「無器官身體」, 而我們都是這原先物質的一部份,我們的身體都是「無器官身體」,徐永旭與其作品也都是「無器官身體」。
就視覺感受來看,此時期的創作在藝術家一個個單元的累積經營下,有著強大的生物性與原生性,是一種增生蔓延的狀態,是單一而整體、組合又分解、斷裂卻聯結的「無器官身體」,如蜂窩、燕巢、牡蠣、珊瑚等的視覺奇觀,這是徐永旭用生命經驗與身體本能反射而成的。而如上兩段所陳述,小單位的創作對於藝術家本人,有一種特別的傳接感受,是種生命單元的置換,一個一個的轉接到作品之上,因此對徐永旭來說那種生命感與存在感特別明顯,是德勒茲的無身體感,小單元在時間的堆積下成就了作品,並不停地堆積、繁衍、流動、生機盎然,而觀者在觀賞之際,也可以充分感受到那當下的堆疊、層次與蠕動,一種生之慾望的勃發,一種竄出與崢嶸的湧出。
結語
即將於2012年2月於台北耿畫廊展出的最新個展『周流‧複歌』,是徐永旭個人過去六年來藝術生命的統整與觀念的再回顧,此時作品的「反陶」觀念與延伸而來的大小單位形式更能一次清晰地呈現在觀眾面前,形隨意走,形隨身體自成,自由線條的展現與大小不一的量體,均在徐永旭觀念完整的表達之下自由自在,思考與行為相輔相成,彼此烘托。自由來自於一種積極的要求與試煉,自由不是沒有章法與隨性,反而是對生命本質與迴圈性的自我體認後,跳脫限制,才有的真正自由。每個人的生命經驗都是一件藝術品,而徐永旭則以「反陶」觀念反其道而形,借用了他逐漸破碎瓦解的身體轉化而成的藝術作品陳述著他慾望勃發與生生不息的生命,自在也自為。
[1] 鄭金川,《梅洛-龐蒂的美學》,台北:遠流,1993,頁104
[2] 龔卓軍,《身體部署-梅洛龐蒂與現象學之後》,台北市:心靈工坊文化,2006年,頁70
[3] 同上,頁70
[4] Barry Smart,《傅柯》,蔡采秀譯,台北市:巨流,1998年,頁188
[5] 雷諾.伯格(Ronald Bogue),《德勒茲論文學》,李育霖譯,台北市:麥田出版,2006年,頁126
[6] 同上,頁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