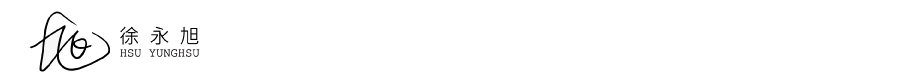「以光織界:徐永旭的藝術世界」- 從肌理微觀到地景仰望 徐永旭無限擴張中的「反陶」之路
外貌予人灑脫不羈印象的徐永旭,言談上總是小心翼翼、謹慎有禮,但溫和中卻又固執到老是別人在喊投降;殊不知,這樣的「固執」卻一直在重新「定義」人們原本認知中的許多事物,包括我們對「陶藝」表現的認知。
2007年,初次與徐永旭合作「創作論壇」展覽時,第一次看到比人還高的大批高溫陶圈豎立在展場中央,還邀請觀眾入內穿梭時,腦內便襲來莫名的恐慌。然而佈展過程中,藝術家除了偶爾皺眉、沉默深思外,感覺不出他對展品有任何的猶疑;到底這個人的自信從何而來?讓人好奇。
2019年再次與他合作《以光織界:徐永旭的藝術世界》展覽籌備,幾次參觀工作室並聽他述說材料應用與改造、燒製研究、成品結構如何加強等細節;終於慢慢理解,他的信心其實是來自於不斷試煉與克服一切的強大念力。
人說,性格造成命運;但徐永旭的「超越」,根本就是他好強性格所造成的「命運」。
父親原籍澎湖的徐永旭,1955年生於高雄市。在初三升高中那年參加了一個重要比賽結果受傷,無法被保送運動專業學校。在高雄中學讀了一年後就轉投考屏東師專,因為穩定的教職可以讓他解決當時家中的經濟困境。
好勝心強,凡事都比別人想更多的徐永旭,在國小教職生涯中同時發展出田徑運動家暨古箏高手之迥異專業形象;1986年接觸到以陶土進行視覺藝術創作的樂趣後,1998年43歲的他毅然決定辭去22年的教職並成為全職的陶藝創作者。
就一位「半途出家」的陶藝創作者來說,徐永旭今天的成就太過「離奇」,但可以想見20餘年前在內、外壓力夾殺下的窘境,然而類風溼性關節炎纏身,反讓他興起比誰都更急迫「要在身體被病魔吞噬前,發揮生命的最大張力。」 的念頭。這迫使他比其他科班出身的人,對創作更為專注且更義無反顧。
長年埋身於塊體不斷擴張中的粘土揉塑,讓徐永旭不得不包裹著護腰,來支撐已然出現疾患的腰椎。一天當十天用的他,習慣以縝密且細膩的思維去規劃每日作息,並精算工作室所費不貲的瓦斯費、材料與人力開銷。但當開始埋首創作時,他會完全拋開這些「理性」,讓手去帶領心靈前行。(圖1)
回歸「手」與「土」原初的親密關係
自從國際性現代陶藝展陸續被引入臺灣後,人們逐漸意識到「現代陶」已讓「陶瓷」步入各種非實用想像;然而步入「當代陶」後,創作者們開始試圖超越陶瓷的「媒材」表徵、衝撞「媒材」原有形貌,甚至背離了「土」的特質。
好奇心十足的徐永旭討厭複製自己,意識到「所謂的創作幾乎都在『紙本上』完成,動手的時候是按圖施工,已經無法滿足在創作中想得到的感覺……。」 之後,他開始拋開對「表象」的執念,轉而尋求作品精神層次上的雋永。
徐永旭認為2002到2006年是創作上最大的轉變期;2003那年他以接近「知天命」之年,進入了臺南藝術大學研究所就讀,接觸到大量的哲(美)學閱讀,與老師、同儕不斷切磋並接受深度啟發的徐永旭,開始養成描述內心思考與想像的書寫,也練就了記錄自己的種種方法。
哲學課程帶領他探究了吉爾•德勒茲(Gilles Louis René Deleuze)、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莫里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等西方大師的理論,也教會他透過反覆辯證與自我質疑去尋找答案。
「思辨」重複出現在研究生活中,徐永旭認真地吸收著東、西方哲學家對事物的分析方式,也讓自己多年來在創作上的糾結獲得釋放。
2005年春天,他到紐約州羅徹斯特美國工藝學校(Ro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R.I.T.)駐校創作並遇到創作上的重大轉折 。Richard Serra與Fred Sandback等人的作品,在他眼前展開一個全新的世界;他們高明地利用單純的材料,戲法般創造了衝擊人類視覺與心理的神奇空間。
受到這些作品的刺激,徐永旭在創作上出現了一些猶疑;亟欲超越的壓力讓他陷入極端的疲憊,只能「漫無目的」地用手揉捏一些小「單元」物件,來尋找靈感 ,但卻無意間讓創作回歸到「手」與「土」最原初的親密關係。(圖2)
那些看起來像散落在大型燒成品旁、有著偶發造形的「單元」零碎體,幾年下來被徐永旭發展出各式組合樣貌;如鱗片般密集的牡蠣殼,如破殼蛋堆累,如熱騰騰、飽滿米粒的完熟飯,或是白鶴芋的佛焰苞等。這些被策展人胡朝聖稱之為「單元」 ,被沈伯丞視為「真菌」 ,被龔卓軍以「孢子」或「青蛙蛋」暱稱 的小物件,像發泡錠瓦解出來的無數「分子」般,讓人感受到極強的有機性。
弧度、深淺不一的「單元」,讓徐永旭瓦解「土」厚重的量體並重組成更大、更輕、更透的結構;碎化的形弱化了作品的「邊」,讓「土」衍生「接觸」、「重疊」或「融合」等更複雜的形式。
徐永旭形容那些「單元」的組成,源自一種「編織」或「築巢」的仿生形體,帶著將觀者眼神吸入的有機「孔竅」,以歡迎之姿吸引生物進入巢穴。(圖3)
同為陶藝家的夫人林秀娘,跟他都對作品中偶然出現窩藏的蝙蝠或小鳥相當興奮,因為這意謂著作品實踐了他的築「巢」意圖,讓徐永旭作品中的溫度並未在出爐後涼卻,而是以另一種形式延續著。
2018年開始,徐永旭在臻於成熟、等待轉化的「單元」系列中,進行類似「縫線」的嘗試。他將在「單元」集結成的塊面上方進行薄土條的覆蓋;乍看之下,這樣的「外掛」為原來作品「畫面」的完整性,帶來詭異的「破」,但當窯燒出爐後,作品上方的土條卻軟柔服貼有如「布」一般的薄透,並碎化出織物般的美麗紋理。(圖4)
為了擴大視覺張力,他也透過「現地創作」,以魚線讓無數「單元」穿梭、漂浮於空中,形成一種有如浩瀚宇宙無重力空氣間的隕石或沙塵。(圖5)
「超越」對於依附窯體、掙脫不開尺幅桎梏的陶藝創作者來說並不容易;徐永旭不假外求,專注於發揮「材料」本身的特質,化整為零,發展出更大的整體,或許是他能將「土」應用到如此出神入化的不二竅門吧!
看似脆弱但實則強大的世界。
2006年刊載於《藝術觀點》上的自述,徐永旭寫道「當自己選擇泥土來當作創作的媒材,如果拋開材料、技術、工具這些問題時,它和自己創作的關係是什麼?」 顯見他看待這項媒材,並非一路盲從於駕馭能力或喜好,而是有著更深一層的籌謀。
長年觀察著土被糰揉、拉展、壓疊或鑿穿的效果,同時測試不同溫度下出爐成品的硬度,徐永旭學會利用媒材燒製後的輕薄與透空,來形塑作品呼吸的「氣場」。當他在工作室中大膽耗資起造超大尺寸的特製瓦斯窯時,野心隨著窯體空間增長,作品也逐漸背離地心引力,促長成驚人的另類「地景」。(圖6為2006年徐南藝大畢業展《界.逾越》現場)
個性踏實的他,一直沉迷於坯土的素燒,單純運用土本身內含的礦物質成分,來燒煉出自然溫潤的結晶色彩,以取代人工感強的釉料顯色;這讓他的作品與大地更為貼近。
當他首次於高美館《美術高雄2006 衍續.重釋:高雄陶》展出巨型陶圈時,不少人曾擔憂作品在公共空間中無法承受外力搖晃(無論是來自人為或自然);但2007年「創作論壇 黏土劇場—徐永旭個展」中,他再度於展室中樹立更多的高溫陶圈,形成人們眼前光影虛實交錯的陶林。(圖7為展出現場,中間組件為後來獲得日本第八屆美濃國際陶瓷器展首獎作品〈2007-6〉)
像強迫症般將土朝「輕」、「薄」、「透」、「高」等極限發展,徐永旭在過程中吃足了苦頭;但他從未將「脆弱」視為作品必然存在的罩門。靠著自學與專家意見交流,他勤奮地上網搜尋並跨國採購各式可摻入土中,改變土質的材料來進行測試。
徐永旭專心地進行著喜憂參半但刺激十足的實驗,相信作品一定可以在不用犧牲肌理質感下,增加堅韌度。在此之前,對抗地心引力的嚴謹計算、材料配方與比例掌握、窯燒温度的熟悉等,都必須有科學的計算先行。(圖8-1、8-2為測試溫度的溫錐)
2007那年,當筆者赴南藝大為《黏土劇場》借件時,一批自窯中出爐、邊緣因高溫龜裂成不規則、有著高低開口的陶圈,靜靜倘佯於南藝大的戶外草地上;佈著斑駁青苔,在大自然光影中起伏的作品表膚予人特殊的視覺感受更勝觸覺。(圖9)
進入展室後,那些原本被橫置的陶圈翻轉成林,層疊的高溫陶有如生物表皮般起伏,中空裡層招引著空氣穿流;無論遠觀或近探,徐永旭的作品總能各具風情且激起不同想像。
徐永旭引人入勝的實驗性陶藝裝置,是一條風險相當大的路;無論是「陶土」還是「瓷土」,媒材伸展、薄化燒煉後的「硬度」也伴隨了「脆度」,在展示上經常處於危險狀態。2007年的他努力地將陶的媒材可塑性做出極大的延展(高度延展到200公分以上,薄度維持在0.5公分左右),到了2019年,兩座近達5米高、一體成形的高溫陶〈2009-1〉,壯觀現身於高美館大廳,讓人不得不佩服他超人的毅力與耐心。(圖10)
除了造形上的突破,他也研究著如何改變作品基座或背撐。
早期以熱軟化與陶圈顏色相近的油土條依附於作品下方重心處的支拄,進化到後來改以更可靠的鐵板內鑲於作品上;每件被高高豎起的作品,擺置重心的拿捏與移運防護,都必須透過對它們結構再清楚不過的徐永旭親自處理。
2019年《以光織界》的展覽中,除了牆上數面「將平面奮力拉展開來」的大跨距半立體風景外,徐永旭在大廳立起的那組高溫陶圈,光是想方設法從被工程團團包圍的高美館外,找到「洞」運進場並將之高高豎起,已然就是件讓人「捏汗」的大工程了。
重達近2噸的高溫陶圈,無論製箱、裝箱、運輸、吊掛、豎立或是反向操作傾倒、再裝箱等,都需要大量具經驗的人力與重型機具如全吊車、貨櫃車、堆高車、龍門架來協助;將每件作品視如生命的徐永旭,在這其間扮演靈魂角色,親自訓練團隊掌握移運與布置的「眉角」。(圖11-1、11-2)
徐永旭如此瞭解「土」與「火」之間的緊張關係,這份瞭解是在無數次試驗與失敗後得到的經驗(或教訓);因此他意識到作品的脆弱會阻斷它們與公眾之間的「和平共存」。所以他也認真地幫作品進行安全「包裝」、「運輸」與「展示」預備,且不惜成本地為每件展品設計方便吊掛的不鏽鋼背撐、卡榫或底座;只有讓作品在「介入」公共空間時,以更「堅韌」、最「無憂」的姿態倘佯於人前,創作才能獲得最大的「自由」。
徐永旭充分了解陶瓷這個材料「被做到最大最薄的時候,它隨時存在著『危機感』」,但他喜歡利用這種走鋼索般的「危機感」,讓自己陷入困頓後,再想辦法走出困頓。 或許就是這種「自找苦吃」的性格,才讓他一路走來辛勞如人飲水,冷暖只能自知了。
「反陶」後,重新定義「陶」
研究所期間的哲學研讀,訓練了徐永旭文字或語言的思考邏輯,與他不斷透過手的勞動來進行創作,是截然不同的生命體驗。幸而他一直都能全心投入,然後又透過自覺來適時抽離,因此當發展「反陶」哲學時,他亦能同步用「技術」來呼應自己的思路。
2006年撰寫碩士論文的徐永旭,經常提起Richard Serra對他強烈的觸動 。Serra擅長的是透過材料最低限的應用,將觀者帶進另一種截然不同的心理世界;徐永旭的「反陶」亦在追求這樣的境界。
他的「反陶」並非輕視傳統陶藝的技術表現;徐永旭解釋著自己的「反陶」邏輯:「在創作的這條軸線上,選擇以『陶』材質本身的感情作為我創作的載體,以極大極薄作為這載體的形式,但我並不是要顛覆它本身或挑戰所謂的極限,而是取用了它傳統優質面的相對性,是它為相異於『陶』的『陶』,將它定義為『反陶』。」
透過自我摸索、不斷嘗試並改變觀看世界的視角,徐永旭由過去專注作品的「表象」,轉向關注「自己」。他在展覽中將自己的情感納入展示中,將創作時強烈感受到的「時間」,透過「自我技術」影像放映,來重播那種溫柔觸感與勞動痛覺,如何交互著心境的轉換。
2007年的《黏土劇場》中,手與黏土「纏綿」的雙向投影便吸引了觀者,步入噴沙玻璃隔成的甬道上;人們看著影像投射著手在土中運行的光影游移,「手」帶著他也帶著你,在微溫、柔軟的泥土中探索前行。(圖12)
徐永旭如此殷切地邀請觀者走近他的作品,是因為那些捏土留下的痕跡,浮現於作品上有如刺青「密碼」,內含了徒手勞動的辛苦、悶熱環境下的汗水淋漓、燒製失敗時的挫折,以及開窯時看到完美成品時的喜悅等記憶;他的「反陶」哲學裡,這些看不見的「幕後花絮」跟作品同等重要。
不管多累,都堅持親手捏塑作品,因此無論是高聳參天的陶圈或如蚵殼般薄脆的「單元」,粗糙、素雅的原色肌理上,都存有徐永旭故意滯留的無數手印;這些都是他珍貴且獨特的「簽名」。(圖13)
正如評論者洪翠霞所述:「徐永旭打從在陶藝界嶄露頭角開始,就不願意跳入陶作的傳統泥淖,做著反覆不變的化學實驗與造型變化的工作,他一直希望自己是社會脈動的觀察者,用自己的眼睛去洞悉人與社會互動的關係。」
當他的作品總以最「危觀」之姿出現於觀者眼前,其實徐永旭正在試圖挑戰人們脆弱的神經線,而他執著以「陶」為主要媒材,或也可視為藝術經營上的某種「策略」。(圖14 為2009年徐在台北當代藝術館展覽《再.之間》現場)
正因為產出的是人們認知中「可能」最脆弱的物質,因此當它們被擴大「視覺張力」時,會產生比其它材料諸如石材、金屬或軟塑料,更具震撼力的「心理」效果;徐永旭喜歡測試觀者的視覺衝擊與想像底限,畢竟這些「心理戲」都遠比單純的造形編排,來得有趣太多。
找到「界」,才能「越界」
徐永旭總說:「當你在創作時,其實作品也在影響你。」為了避免長期的捏塑創作,最終淪為一種不斷複製自己的「機械」行為,透過叛逆的「反陶」思維,他也在不斷釋放自己的疑惑、挑戰疑惑並解決疑惑。
正如他所意識到的「越界」:「你要找到『界』,才能『越界』。」也是因為他徹底了解「陶」的「界」,才有辦法「反陶」。過去,他生命中最無法掌握的可能是窯爐中等待煉燒成形的作品,但如今連這項不易掌握的事,都在爐火純青的技術下變得不再難以想像。
他的藝術語彙,早已超越人們認知中的「陶藝」,步入當代藝術最核心的表現範疇,同時也突破了媒材、技術與設備發展上的極限,成為國際罕見案例。
2008年7月,徐永旭參加日本美濃國際陶藝競賽,在五十多個國家、三千兩百多件參賽作品中,以大型雕塑〈界.逾越〉拿下首獎,為台灣摘冠的第一人;那是他才開始正式當一位專職藝術家10年後的事。
總是混身大批人群中「跑馬」(馬拉松)的他,看似有無數競爭對手,但能幫自己抵達終點的還是只有自己;徐永旭非常了解這點,所以一直以來也只專心在對付「自己」。
開展後又再度出國「跑馬」的他,在這條望不見盡頭的創作路上起跑後,其實早就已經有「跑就對啦!管他盡頭在哪!」的覺悟。(本文轉載自高雄市立美術館《藝術認證》雙月刊第8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