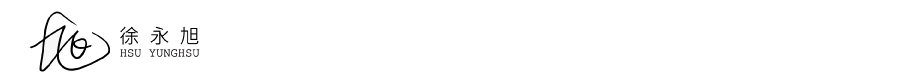「以光織界:徐永旭的藝術世界」- 來自「織光現場」的報告 「徐永旭展」的策劃經過
相識
徐永旭和我的相識,從一份收到的電子郵件開始:二零一二年某日下午,台北胡氏藝術將徐永旭作品的圖片傳到我們新加坡事務所,建議作品掛在剛竣工的「忠泰繹」大廳牆上,作為該棟大樓的收藏。問看這件藝術作品是否與我們設計的建築風格合拍。
水漾波浪帶狀的造型分好幾條,白瓷表面又散放附著了好一些,既像蚌貝又似蛋殼的同材質物體。貝狀蛋顆彷彿在做另一種的跳躍,讓原本橫向流動的畫面,增加了上下浮盪的動態。
(圖1-2)
「忠泰繹」是在松山車站與五分埔之間的住宅案,設計靈感源自於那一區的橫街窄巷,我們將浮現出來的街巷化為數條垂直的「城市緞帶」;在建築立面以白色水晶玻璃建材,把粗筆畫線條勾勒出來。
我望著同事遞給我的徐永旭作品的圖片,心想:這件藝術作品從天而降,怎會如此的與建築物不謀而合?
掛在「忠泰繹」大廳牆上的這件作品,後來還有段小插曲:要襯托出這件作品的瓷白色澤,若能用材質較粗暗且含線紋的高溫陶板來墊底,最為理想。可是背板得要比一般貼牆的陶瓷磚塊的尺寸闊大,才能呼應這件藝術品橫向的比例。
當我把想法告訴徐永旭,他立即回覆說這個他能做到。數星期後我便收到快遞寄來的陶製樣板,正是我要的深褐色,質紋又有好幾個選擇。
這些年來,徐永旭與我的交往,就是類似以上這樣的切磋。我們兩人都是輕度工作狂,閒餘時間不太喜歡在自己的專業圈子應酬。徐永旭在家周圍跑步練習馬拉松賽我則愛游慢泳,兩樣都是清理腦筋的孤獨運動。
所以當徐永旭一口答應承擔下新加坡「勝樂集團」(Select Group,2014年)總部大樓的外立面專案時,我心中雖暗喜卻不吃驚——徐永旭再次接過棒往就前直衝奔跑,我這才知道,他接受挑戰的能耐和毅力相當驚人。
「勝樂集團」建築立面乾掛的弧形褐土色陶板,表面上明顯留下手指劃過的淺溝線條,在猛烈無攔的熱帶陽光下照曬,遠看像蒸港式點心用的竹籠子。大中小三款共有二千多件,四牆圍繞五層樓高,無異是件超級壯觀的現代藝術裝置——遙遙呼應了Christo 在倫敦海德公園蛇形湖中,堆疊而起的大油桶。雖然Christo的現場藝術裝置,是後來(2017年)的事情了。(圖3-4)
陶與力的關係
片陶只瓦與建築的關係向來密切,但傳統上的屋陶瓦用來蓋屋頂、排雨擋陽。以這樣誇大的尺寸,又大數量的高溫陶板乾掛於墻上,對我或對徐永旭而言,無疑是個空前的新鮮嘗試;雖然陶板主要的功能是用來掩蓋背後的通風口,緩衝進出中央廚房的風速,它亦體現了建築與藝術互相跨越的一個「界面」。
在進入窯燒階段前,將陶瓷原土堆積至極大規模、材質捏壓至極之薄化,似乎是徐永旭在創作時所愛做的事情。這和羅馬時代、中古時期西洋建築用磚或石砌,堆疊成聳高的拱門,或聖殿裏巨大的穹頂,異曲同工。
在十四世紀,意大利的翡冷翠,教宗與他的建築師們,在大教堂拉丁十字平面的正中央,塑造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大空間。旨在希望信徒齊聚朝拜時,身處其間能驚訝它的雄偉,讚嘆造物者的神奇。只不過石柱之間的跨距實在太大,多次建蓋的嘗試都不能成功,多年之後仍無法為之封頂竣工。
時為1315年。直至1418年,經歷了百年之久,四十歲出頭的工程師菲利普•布魯内列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用了築有蜂巢橫膜的雙層薄牆,才將翡冷翠大教堂圓屋頂的問題迎刃而解。
巍峨站立在高美館大廳裏的「2019-1」之作,是這次徐永旭個展先聲奪人的一首序曲。它在第一時間就懾服人心,來者看見徐永旭再次突破陶瓷材質所能做到的闊度和高度,無不嘆為觀止。不期然我想起菲利普•布魯内列斯基的膽大心細,以及上述翡冷翠大教堂的穹頂——宛若毫不費氣力,赤手造出數重山。
高美館展
高美館「以光織界」展的設置,經過了藝術家、美術館、我們的事務所三方多輪的探討。從素描、電腦、模型,對展出空間的模擬、作品擺置的位置、至現場最後一刻的定案,全程與徐永旭的推敲一來一往像在對打一場愉悅輕快的網球賽。這讓我醒悟到,之前與他的合作,過往所有的經驗,彷彿是為了籌備這事,先打好基礎。
徐永旭的作品呈獻的質感與大刀闊斧劈砍出來的木雕刻既相異卻又有其相似的地方——它們都藉著投射其上的光芒,以及因而發生的影子,來鋪陳敘述作品之上各個部分的體感。在這光與影裏,我們目睹到千百次細緻的碰觸、按捏、揉壓、撫摸、擺放,藝術家與陶土親密的關係。於是攀藤粗莖上,綿延不絕冒長出一朵兩朵無數朵喇叭闊盆的花卉,或是槎枒樹枝上群蝶破蛹而去,留下無數空蛋殼窩居。一件件都是藝術家時間的紀錄、有關生命的比喻。在萬象繁雜的現實裏,瞬間靜止下來,徐永旭的作品帶觀者回到一切眾生的源頭。而藝術家有意無意,於作品上四處經手留下的指紋,其私己性,相較於刀削斧劈的木雕作業,還要更細膩、感性,令人心動了。
經近年內部裝修後,高美館104、105室兩個展廳變得現代、簡潔。打從一開始,策展方向就決定好要讓展覽與這兩個空間相呼應;並且希望二室的效果為一明亮一微暗,讓觀展的經驗更富層次感。在策劃的過程中,我一直自稱為「黑衣人」,要把建築參與的部份儘量隱去,連懸掛作品的細部都要崁藏牆裏,不讓任何設計外露。
作品最終或站或掛在展場的舞台上,單純地因為光線的投射而表情多樣。沒有刻意添加的背景或道具做成不必要的干擾。就似能劇演員的一舉手一投足,隨即形成的畫面,永恆凝留在觀者的印象中。演員行走、停留、迴轉的動態在這裡必須由觀者來完成,作品與觀者互動,前者傳遞給後者親暱的私密感。
進場 展間一
展間一的104室中央擺放的兩對雙屏風作品,引導甫進場的觀賞者依循它們的排列而環繞,測視。八件作品分別以四個長腳鋼框架來支撐和豎立,鋼架前後兩面懸掛了高約三米至三米半的「2018-32」白瓷作。四幅作品都左右錯開,之間的縫隙,正好允許視線穿越過立屏風,張望對牆上的巨大瓷土作品「2018-15」的組合,或是側牆上比較小巧、深色的高溫陶土作品「2018-11」。雙屏風擺下的無形廣場佈局,塑造了一個前、中、遠距的立體景深經驗。觀者在步行游走間,透過近物看遠物。
進場之後,囘看展場入門處千絲萬縷的蜘蛛網,作品「2019-9」是件就地創作,在天花、牆面、地上以碳纖維尼龍綫多番縛綁成狀。其景深的層次比「雙屏風」更深遠,但只供目眺而身軀不許靠攏或碰摸。附著在尼龍綫上的白瓷殼物體載浮載沉,遠望像深夜睡躺在草坡上,仰望蒼穹裏大小不一,數之不盡的恆星。星辰們似遠又近,無的在半空中炸射散分,滿佈眼眶,視覺可觸及的週圍。
視線、軸線、動線
一開始我們就明白,作品擺放的位置將決定人們觀展時所採取的視線與角度,這也包括了在展場內行走時的動線。每件作品擺放之前,徐永旭和我的工作室都各別做過模擬與測試,來推敲與確定作品位置的設計。(圖5-7)
104室與105室作品的擺放,有如在弈兩盤大相徑庭的圍棋,棋子佈陣不同,所得的棋局效果也各異。104室展間一所展的作品主要為白色瓷土,配合也同時增加了展覽室的光亮度。到了105室的展間二,所選的作品則顯露出更多樣的顔色與光澤。曲虹形狀的「2017-28」白色高溫陶,竟是稀有的鵝黃色,即便是一貫「無添加」的高溫陶土,宛如蟻窩或蜂巢的「2019-5」,内外面似挖掘打開的地層土壤,赤褐的肌理呈現了深淺多層次的變化。
「2019-5」窩巢建物刻意擺得像迷宮,豎立的城牆又剛好超過一般人的高度。人走在其間的狹窄通道,立即被土城圍攏,辨別不到方向。僅能順著彎曲牆面放慢前行,壓迫之感和視覺只在偶爾開洞的牆面,可以暫時舒緩一下。穿越洞孔可望見的,其實不過是同樣的土質,以及其上藝術家親手壓捏與紡織出來,更繁多的遠近難分的光影。
進退 展間二
展間二裏每件作品的位置看似隨意擺放,無一平行亦不講究對稱,但環扣出來的是作品與作品之間緊密的關係,從而吸引觀者的參與、互動、進入或退出狀態。距離「2019-5」迷宮群作不遠處,有件造型和宮裏眾作極相似,土質卻非褐陶的白瓷作「2015-15」在梯級旁側的離隊兒有點孤芳自賞,但也因而拉出長遠的一條軸綫,將觀者牽動。
倘若細看,在不顯眼的室内角落兩端各有一件瓷土之作(2018-9,2018-10),微型作品靜處在牆角的不鏽鋼板台上,遙遙眺望,又仿佛在對話。它倆在角落獨自發光,組成另條軸線,橫空劃過,飛越在半空與原有的軸綫交織。
展間二存有的軸綫正如之前的蜘蛛網作品「2019-9」,無形卻含極度磁場及引導力,不知不覺間將人與在展的藝術物件串連起來。
全景 借景
高美舘105室廻迂曲折的佈置,不禁令人聯想到蘇州庭院裏,亭臺樓閣的格局。除了前述展間二的大空間,人們還可以拾級而上,步過光廊,折返至一道可俯視展間二與展間一的長廊,讓人從不同高度、角度觀賞過展覽的全貌,然後才算大功告成。
一樓半的光廊在新改造的過程加建了好幾根直竪的板柱,將原有的橫向窗戶打成垂直長條形,更像傳統明式窗框的比例了。窗外的樹木綠草地依然沒變,陽光、雲朵、細雨也都如常。觀者步行至此往往被戶外的景觀吸引了過去——方明白原來藝術在模仿捕捉的,皆是大自然的美。(圖8)
五件靠在玻璃窗前的「2019-7」瓷作,清脆如深海裏剛附黏而成的白珊瑚礁,圈點出的正是這個道理。(2019.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