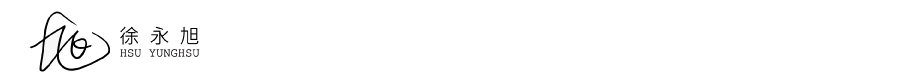影的玩味:全球脈絡中的徐永旭藝術
藝術家肖像,黏土創作
2015年,一張藝術家徐永旭在台南的工作室照片被拍攝了出來,照片令人得以深入洞察他令人歎為觀止的陶藝裝置的創作過程。[圖1] 那是一幀黑白影像,從高處的視角往下拍攝,讓我們得以鳥瞰寬廣的長方形室內空間的整體狀況。沿著最左方水泥牆排列的是細緻的黏土群,彼此纏結而成為藝術家特有的精細之作,這些錯綜複雜的有機形體成為他的雕塑組合體的建構團塊。在最右方的前景,我們可看見一件2公尺高的高聳橢圓形結構的一部分,那是由厚實的骨白色緞帶造型瓷土所構成,令我們得以一窺徐永旭大型系列作品的驚人尺幅,以及其製作上所蘊含的精巧技法。占據照片中央的是一張長桌,桌上佈滿生坯──覆蓋著透明塑膠布的小型、仍然柔軟且尚未燒製的物件,它們就如考古發現物一般,正等待著被檢視。
除了這些靜止的物體之外,工作室猶如一個繁忙的蜂巢。二十幾個人物分佈在室內空間,或環繞著中間的桌子,或從房間的一端跨步走向另一端,也有人手握持著工具或處理著黏土,低頭專注於手中的物件,身軀因為移動而顯得模糊。這些人物就像工廠中的工人,穿著一致,雖然他們都身穿黑色T恤與牛仔褲,但奇特的是,每個人的額頭上都綁著一條白色毛巾布的防汗帶,就好像參加訓練嚴格的團隊運動。這些人物之間詭異的相似性令人感到不安,直到我們瞭解我們所看到的是一張多重曝光的照片。如此一來,我們看到在工作室中忙東忙西,所有相貌一致的「工作人員」,事實上就是同一個人──藝術家本人──在一段長時間的黏土創作過程的許多時刻中被捕捉到的身影。
事實上,要將又重又濕、難以駕馭的黏土塊形塑成如此大量而不可思議的輕盈精巧的形態,其中所需的勞心費力似乎是超乎單一個人所能承受的重任。然而,就如照片所示,如此的勞動重擔便由徐永旭單槍匹馬一人承擔。這幀影像宛如藝術家工作中的肖像,記錄了創作這些雕塑奇觀相關的高度技術水平與不屈不撓的恆心耐力,讓徐永旭為每件作品耗時費力的投注過程得以為人所見。
誠如藝術史學家羅莎琳德‧克勞斯(Rosalind Krauss)在她深具影響力的論文中對美國藝術家理查‧塞拉(Richard Serra)自1986年來的觀察,她認為藝術史被「著名的藝術家工作肖像所鑲嵌。」 這令人立即想起畢卡索(Picasso)、馬諦斯(Matisse)、帕洛克(Pollock)在他們的工作室中的那些令人回味的照片與影片,每個影像都訴說著「有關藝術家的個性、毅力、直覺、巧技、成就的更大舉動」,其方式似乎也囊括了藝術家的整體創作,包括起始、中間過程與結尾。克勞斯既將塞拉列於這個令人敬畏的藝術家系譜中,又使其與之對立。她專注於一張藝術家在其工作室所拍的深具意涵的黑白照片,藝術家在照片中「戴著頭盔、護目鏡、防毒面具」,有如「著裝上陣」,正對著一個看不到的目標擲甩熔化的鉛料。對克勞斯而言,這張藝術家擲甩鉛料的肖像強而有力,顛覆了現代主義的宏大氣勢。其原因有二,一是防毒面具的出現,這著實將有關藝術天賦、表現性及個人特質的浪漫化概念消弭殆盡,同時並指涉工業勞動的去人格化。原因之二是我們所看到塞拉正在創作的「藝術品」事實上並未被照片畫面所捕捉。我們所看到的就只是塞拉的姿勢──創作的動作──克勞斯提醒我們,這是「被剝奪了物件後的動作,與時間具有極為特殊的關係(……),這項行為只有動作,動作,再動作。」這為現代主義的敘述性目的論帶來迥然不同的挑戰:故事可以有起、承、轉、合,但不一定要循序漸進地發展。
徐永旭在其工作室的肖像也具有相似的混亂性,對身為台灣藝術史關鍵人物的徐永旭而言,這對以下二者提供了有趣而機警的回應,其一是針對在正規的歐美架構之外的「遲來的現代性」概念所產生的嚴重焦慮,其二是瞬息萬變的「全球當代性」的定義。有別於在一個靜止的或「醞釀的」時刻中呈現出與藝術品奮鬥的單一、個別的英雄人物形象,我們看到的是藝術家在創作中的多重版本,那是在無法縮減的時間流程的數個時刻中所拍攝的。相對於塞拉戴著防毒面具、護目鏡、頭盔而「著裝上陣」的好戰影像,徐永旭顯得完全沒有防護,而且不受阻礙。他額頭上所綁的白色防汗帶不僅是對於身體力行與手作勞動的實際作為,同時也展現陶瓷製作的持續性,以及藝術家對於藝術創作不辭辛勞、全面投入的態度。年已64歲的徐永旭仍然積極參加世界各地的馬拉松賽跑,為了這些賽事的訓練,他在工作室周圍的田野間長跑,每週數次。就許多方面而言,與長跑一樣所須保有的體力、適應力及耐力不僅讓他持續拓展藝術媒材的界限,同時也使他得以在自己預測的步調與時間內達到此目的。
形式的問題
事實上,徐永旭的藝術生涯有些迂迴崎嶇。1955年出生於台灣西南部的港都高雄,就讀於現今的屏東教育大學,同時也學習成為古箏樂手。當他於1975年畢業獲得教育學位之時,他對此項具挑戰性的傳統撥弦樂器演奏已是得心應手,他在數場音樂會中演奏,並屢獲好評。當朋友介紹他接觸陶藝之後,他將學習音樂時的決心與自我要求投注於媒材的實驗之上。他於1986年成立自己的陶藝工作室,並於1992年師事知名的台灣陶藝家楊文霓,在其教導之下創作。1998年,徐永旭在43歲之時做了艱難的抉擇,脫離當時仍是較為穩定的中學教師及專業樂師生涯,以便全然投入黏土創作。在此高度競爭的領域之中稍有所成之後,2003年徐永旭於48歲之時進入台南藝術大學就讀,成為攻讀美術碩士學程中至今年紀最長的學生。
相較於像攝影與影像這樣的新媒材,黏土創作需要藝術家這部分極大的投入:包括身心與物質的投入。黏土不僅讓選擇將這項笨重的物質雕塑成形的藝術家勞心勞力,同時購買這樣經常是進口的沉重原料的成本,再加上長時間高溫燒製的花費,也都造成財務上的耗損。儘管如此,這就像是精細的煉金術。在準備階段,陶土本身結構上極細微的改變、處理時的疏忽,或是燒製時的缺乏經驗,都容易使得作品在窯爐中崩壞。因此,徐永旭的生涯轉換便是一場存在著風險的冒險,無法保證具有明顯的回報,不論是藝術上或其他方面。
此時,值得提供一些與徐永旭選擇專注於藝術創作之時有關的脈絡,緊密觀察台灣當代藝術的發展,並結合1990年代與2000年代世界其他方面的狀況。1987年台灣社會、政治、藝術的歷史關鍵時刻,象徵40年專政獨裁的終結,並激發台灣本土認同的追尋。1990年代一連串的政治改革,如1996年首度的民主總統選舉,促進了這些時代的改變,恰巧此時在國際藝術圈也發生更廣泛的「全球性轉變」,激發從邊緣對藝術的興趣,以及全球各地當代藝術雙年展的開展。 台灣於1995年初次參加負有盛名的《威尼斯雙年展》,使得這個島嶼國家現身於全球藝術地圖之上。由台北市立美術館於1996年舉辦,具歷史性的《台北雙年展》則催生了急需的藝術辯證與批判論述,而且是針對台灣的國家與藝術認同、本土性與國際主義的問題,以及藝術在快速轉變的社會中的角色。
因此,在當時台灣國內外受到最多評論關注與學術辯論的藝術作品便是直接對於「民主化的社會政治情況、後工業化、變化中的大陸與台灣關係」有直接回應的作品。 這些作品的形式經常是具有公共性、參與性、社會投入性的藝術項目,透過藝術介入、暫時性行為、錄像與紀錄影片動員當地社區,就如陳界仁、吳瑪悧、黃博志的作品,他們的作品也在國外多處展出。同時,世界各地的藝術家採取了藝術挪用、關係美學、後現代模仿等策略,創作出大規模、沉浸式、參與式、民粹主義的作品,與逐漸茁壯的藝術界血親及新自由的全球化行動相互共鳴。 例如,旅居世界多處的台灣藝術家林明弘經常參展國際性展覽,他大片的地板裝飾作品運用了台灣居家室內裝飾與大量生產的俗麗花布美學,模糊了高雅藝術與通俗文化之間的界線。
當有些人樂見於藝術世界自1980年代後期以來的全球性拓展,包括以全球主義及多元文化主義的精神而擾亂藝術規範中的歐美中心之時,也有一些人感嘆這是文化同質性萌生的指標,在其中所有異質的徵兆都更加被含納於跨文化循環與跨國交流的洪流之中。這些發展造成一個令人擔憂的結果,也就是非歐美藝術家必須默默而特意地凸顯他們的國籍、種族及社會政治立場,以滿足全球藝術市場喜好異國風情的胃口。無庸置疑,來自邊緣而想在國際舞台上揚名立萬的藝術家當時(而且可以說現在仍是)身陷困境。選擇在作品中諷刺地運用易於識別的文化政治指涉性符號的藝術家被指責為「銷售一空」及「迎合」市場,而那些在創作中專注於形式、媒材、概念範疇,而不展現其文化與種族淵源的藝術家則太常被視為只會「模仿衍生」:太遲且盲目地採用歐美前衛的通用語言,只為了商業所得。 因此,就如藝術史學家瓊安‧基(Joan Kee)嘲弄地說,從那時候開始,非西方藝術家便一直被一個問題所困擾:「當人人都只想知道你來自何處之時,為何還要在形式的問題上花費心思?」
此段對於1990年代與2000年代藝術發展的簡短且絕非全面的概述說明了徐永旭決定於此時期開創陶藝家生涯並非是迎合以下二者:一是當時台灣流行的以社會為導向的前衛創作,二是「全球當代」的舞台上對於非歐美藝術家的異國風情需求。畢竟,對於許多台灣藝術家以紀錄性寫實主義及公共執行而高度探索的政治社會議題,不能說徐永旭的陶藝作品與此有直接關聯。此外,表現出徐永旭雕塑集合體特色的有機、活力充沛的造型並無法立即被識別為「具有台灣特色」,因此相對於為迎向那些渴望具有易於辨識的文化差異特色的私人收藏家與公共機構而日益增加的作品,徐永旭的作品可能容易相形見絀。相反,徐永旭長久以來在他的藝術實踐中一直關注的正是「形式的問題」。
讚頌雙手
在台灣藝術史教授廖仁義觀察徐永旭作品的論文中,他將徐永旭的創作分為五個形式發展階段:生機主義(1992-1997)、超現實主義(1997-2004)、抽象表現主義(2004-2005)、過程藝術(2005-2012)、形而上美學(2012迄今)。對於廖仁義決定以歐美現代主義及新前衛傾向的架構而對徐永旭的創作加以分期編年,有些人可能會有所異議,但廖仁義的分類仍然是具有啟發性的。 直到2005年,徐永旭創作了小型或大型的奇形異狀、具生物形態且強而有力的雕塑,充滿異常自信的抒情表現,對於一位多年來受到音律薰陶的藝術家而言,可謂相得益彰。我們確實可在這些作品中觀測到現代主義的標誌性人物所賦予的影響,如亨利‧摩爾(Henry Moore,1898-1986)、芭芭拉‧赫普沃斯(Barbara Hepworth,1903-1975)、尚‧阿爾普(Jean Arp,1886-1966),但同樣地也可對照於知名的台灣雕塑家朱銘(生於1938)或新加坡雕塑家黃榮庭(1934-2001),尤其是徐永旭一系列探索造形極限的大型戶外陶瓷雕塑。
2003年就讀於台南藝術學院之後,徐永旭受到龔卓軍教授(現任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博士班所長)的影響──對於克勞德‧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加斯東‧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莫里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等結構主義學家、後結構主義學家及現象學思想家的作品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徐永旭早期作品的名稱,如2000年代早期的《神話》系列,即暗指著這些概念在理論上的影響。然而,很明顯的是徐永旭努力地想將這些研究化為實際創作。《神話》系列中多種排列的陶瓷造形顯示了造形的不確定性,包括從大型、戶外坐姿人物的原始探索到垂掛於破舊木塊上的小型、縝密、細微、青瓷色彩的物件。[圖2a及2b──《神話4》及《神話18》]
之後在同年所發生的兩件事深刻改變了徐永旭的藝術方法論,尤其是他的造形語彙。當時,徐永旭正創作一系列平滑、像葉子般的容器,其異常細薄的黏土就像是脫離紙張或畫布承載的筆觸。這些立體表面上高彩度的朱紅或紫色長條裂痕令人想起盧齊歐‧封塔納(Lucio Fontana,1899-1968)或安尼施‧卡普爾(Anish Kapoor,生於1954)的作品。這些創作於2004至2005年間的系列作品說明徐永旭逐漸熱衷於藝術史,以及藝術物件對於觀者的影響,例如就像是表面平滑的穩定感與具有動勢的切口的強烈感之間的對比性,或是不同色彩在我們理解空間與深度時所產生的效果。[圖3a及3b──《2004-16》及《2005-5》]
然而,徐永旭於2005年遭遇一場嚴重的車禍,使他立即發自內心體會到人體的脆弱,打消了任何對於知識反省或視覺沉思的藉口。就如之後他對此經驗描述道:「回到工作室裡坐立難安,生死一瞬間的恐懼不時侵襲著我,因此強迫自己將手進入泥土中,一下一下的推動和搓揉,情緒也隨著手的進行,物件一個個的出現而漸漸平穩下來。」
意外發生之後,徐永旭以雙手直覺地創作黏土,以一種幾乎是強迫性的姿態將此種柔軟可塑的物質揉捏、形塑成易於處理、手掌大小的型態。這種神經質的習性產生了療癒、甚至是冥想的特質,很快成為一種儀式,且之後被納入其藝術創作方式之中。 由於此種對於身體的焦慮,徐永旭揮別早期作品柔軟、流暢、類超現實的造形,開始將黏土形塑成小型的、粗製的、像杯子般的容器,充滿表現藝術家身體存在的指標性符號──按壓成淺表凹痕的指紋、因神經能量激發而凹陷、變形、升起的黏土量體。每一單件都迴響著具有動感的能量,從藝術家的雙手傳達到物質,然後又再注入窯爐的熱度。起初,徐永旭並非為了任何名義而創作這些手部操作的微小物件:它們只是他為了逃避縈繞心中的「死亡恐懼」而在工作室中打發時間的方式。
事實上,就如同哲學家提姆‧英戈德(Tim Ingold)的觀察,黏土這種媒材本身就立即暗喻著肉體性,其實就是終將一死的特性。畢竟,陶器曾經是最早且歷時最久的人類文化與文明的展現。不論是在它們操作與燒製的過程中、以功能性物件的身分存在,或是存在之後轉化為過去遺留的文物,陶器都像是生命體一般,容易具有「長期不穩定性」──持續受到「解體或蛻變」的威脅,需要「警戒與照護」。 依藝術史學家葛倫‧R‧布朗(Glenn R Brown)所言,「一個功能性陶器的自然生命就像是某個生命體一般,滿載著風險。器物上的傷痕──刮痕、缺口、裂紋、褪色──都是陷入風險的證據,訴說著真實的經驗。」 雖然布朗此處所談的是日常陶器的「社交生命」,但在思考徐永旭此時期的藝術產物時,布朗對於陶器如何可能透過雙手製造、操作與使用的有形痕跡而「訴說真實經驗」的想法也是可供運用的。
雖然徐永旭在2005年的意外發生後開始創作這些杯形容器,但直到2008年才開始將其堆疊與結合而成為雕塑體。這些作品一開始是相當小型的尺寸,如作品《2008-12》[圖4- 2008-12]只有29公分高,53公分長,由數十個這些手掌形狀的單元所組成,壓製在一起,且高溫燒製而為一個具有泥沙感的陶器混合體。製作出的成品既具泥土特性又純樸粗獷,但同時也顯得迷人細緻且有機生動,像是原木上叢生著菇類的耳狀突起物,或是傳統中藥及烹飪經常使用的黑木耳。
這些早期的手作零碎物件與造形的完美性及藝術技巧之間極少關聯,相反地,它們令人想起超現實主義者喬治‧巴塔耶(George Bataille)所說的「無形」(l’informe)。對巴塔耶而言,無形立即顛覆了高雅藝術的理想化概念,回歸到基礎物質性的層面、身體及其動力的實踐,以及日常生活的範疇。 藝術史學家伊夫‧阿蘭-博瓦(Yves Alain-Bois)與克勞斯於1996年在龐畢度中心策劃的知名展覽《無形:使用者指南》(L’informe: mode d’emploi)將巴塔耶刻意定義不明的詞彙加以發揚光大,對此二人而言,無形具有解除的力量──它是反形體的,僅僅只是「操作的集合」,取消並破壞極端現代主義(High Modernism)本身的規範與意圖。
一年之後,徐永旭於2009年開始使用高領土,並以更高的溫度燒製,製作出多元而不規則形狀的骨白色容器,沒有太多的彼此相壓及結合,而是細心地層層堆疊與相連,每個貝殼狀的殼形物都保留其脆弱的形狀。他繼續製作一系列白色的霧面瓷器結構,就像是蠶繭巢穴,或是鈣化的白色珊瑚群。[圖5a及5b – 2011-38及2013-13]
如果這些早期具泥沙感的變形,或事實上是「無形」的實驗性結構單元是出自於藝術家自己對於人體的脆弱性及其自身的必死性而產生的即刻焦慮,則其較後期且持續進行的細緻瓷器殼狀物系列似乎顯示出藝術創作可透過重複動作而卸下精神創傷的負荷,也就是透過重複的手部操作及習慣性的單純力量。雖然每件瓷土容器比陶土物件在重量及用色上都更為輕盈,但這些瓷土容器卻被結合為更緊密、更複雜的結構。事實上,徐永旭開始以逐漸提高層次的建築意識與技法將這些零碎物件堆疊在一起。這就好像似乎只有透過對技法及材質的精通熟練,徐永旭方能超越一開始就令他煎熬的「死亡恐懼」。
2018年,徐永旭創作了一件起伏狀的壁面作品,290公分高,850公分長,40公分深,由層層的瓷土杯狀物所構成,並分佈著按壓於作品表面、如溪流般的扁平條狀黏土。[圖6 2018-15]雖然具有黏土的重量與製作建造時所需的費力耗時,但當此件作品裝置於牆面而從遠方觀看時,卻顯得不可思議的輕盈且令人印象深刻。這樣的經驗令人迷惘,就像是迷失在森林中,透過如網格般的枝條與似乎無窮無盡的枝葉而望向遠方。
近觀此件作品則會開啟不同的感受範疇。不同於早期實驗性的泥質陶土物件所具有的混濁感與堅固性,瓷土不可思議的細薄透明性為我們與藝術品的邂逅再度注入脆弱的元素──遺失、崩解、毀壞的遭遇。同時,藝術家重複以其雙手與手指揉捏按壓黏土的動作可能被解讀為其肉體存在及生存於世間的肯定,並成為減輕此種威脅的一種方式。藉此,我們可認為此作品見證了人類生命富有的適應力及面對生存的不確定性時所產生的創作力。畢竟,徐永旭在處理的過程中,已將其特有的身分符號確切地烙印於黏土上。纖細而薄層的藝術家部分指紋嵌入每件作品的表面之上,那是存在的痕跡,不僅忍受了無法承受的窯爐火候,同時也因此而變得更為強韌。
誠然,徐永旭的作品經常被描述為需要耐力的藝術。其創作的手感與觸感──尤其是在其各種手部造形的組合單元上顯而易見──曾受到廖仁義的評論,他所討論的是藝術家在適應特殊的黏土形態需求時,其自己身體所承受的生理壓力。依廖仁義所言,我們無法想像「為了適應黏土這種媒材,[徐永旭的]雙手曾歷經重新塑造的緩慢過程」,尤其徐永旭是個經過數十年長久訓練的古箏樂手。就如廖仁義所述,「當一位樂器演奏者的手指承受著抵抗樂弦阻力所產生的一定程度的傷害,則一位陶藝家必須忍受來自黏土令人更為艱辛的阻力、磨損與侵蝕,即使他的姿勢必須從優雅的坐姿轉換為辛勤勞動的姿態。」 雖然本文開頭所引述的藝術家在其工作室的照片令人確切地感受到藝術家就像是個「辛勤的勞工」,但這可能仍無法捕捉到藝術家手工技藝中的物質親密性:藝術家對黏土的觸感反應,以及其手掌與手指壓力的細微動作。
事實上,製作手法的感知,以及物質與製作者之間接觸的相互作用,長久以來一直是藝術史上喜好評論的主題。法國藝術史學家亨利‧福西永(Henri Focillon)在其著名的書籍《藝術中的形式生命》(The Life of Forms in Art,1934)中名為「讚頌雙手」的章節之中以明顯的現象學語彙討論手工製作的品質:
世上的知識要求一種觸覺上的鑑別能力。視覺從宇宙的表面一掃而過。手部瞭解一個物件的具體量體,是光滑或粗糙,是與天上或地下相連而無法分離。手部的動作定義了空間的空洞與占據空間的物件的盈滿。表面、量體、密度、重量皆非視覺的現象……他並非以他的雙眼來測量空間,而是以他的雙手與雙腳。觸覺使自然中充滿神秘的力量。缺乏觸覺,自然就像是魔法燈籠形成的宜人風景,輕微、扁平、虛幻……
對照以滑順的視覺性來觸摸、處理、感覺而產生的直覺立即性,福西永質疑視覺的首要性,以及因此而表現出現代性經驗特色的視覺體制,這視覺體制在我們當今高度視覺化的時代中受到更多的宣揚。視覺停留在宇宙的「表面」,而探索性的雙手則具有精細調節的感受器與對握持物體的感應性,能夠「透過」物質進行操作,與物質達到親密的接觸,以至模糊內與外、表面與實質之間的界線。
福西永的研究強調藝術家與物件、製作者與物質之間的相互關係,其研究也預見現象學的轉變將成為之後藝術發展的特色,尤其是1960年代後期與1970年代極簡主義與後極簡主義的盛行。 在此段時期中,尤其在美國,藝術家開始對於空間、時間、移動、存在,以及藝術相遇的過程所具有的物理與經驗特性進行實驗,以此駁斥現代主義所主張的視覺至上。此種對於藝術相遇的感官與現象學方面的喜好也成為徐永旭創作的特色,尤其是在2005年之後。
就如上文所述,當年所發生的兩件事造成徐永旭在藝術手法與形式語彙上的重大轉折。如上文所論述,其一是藝術家的車禍意外,這導致他持續創作出一系列手掌形狀、單元組件的組合式黏土結構。其二是與極簡主義及後極簡主義藝術家作品的親身接觸,這造成他劇烈擴充了作品的時空與現象學層面。
當徐永旭在美國羅徹斯特擔任駐校藝術家時,他與另一位駐校藝術家展開一次即興公路旅行,造訪紐約上州的迪亞藝術基金會(Dia Art Foundation),就實在那裡,徐永旭第一次直接接觸到了理查‧塞拉(Richard Serra,生於1939年)、法蘭克‧桑巴克(Frank Sandback,1943-2003)、麥可‧海澤(Michael Hiezer,生於1944年)等藝術家的作品。當時,徐永旭不僅仍然致力於克服車禍的後果,而且也奮力找尋形式上的藝術表現方式,期望能在物體的「表面」之外與觀者取得共鳴。
與迪亞藝術基金會永久典藏的塞拉作品《扭曲的橢圓》(Torqued Ellipses,1996 -2000)的相遇格外令人「動容」,同時這也意味著「移動感」。受到義大利建築師法蘭西斯科‧博羅米尼(Francesco Borromini)在羅馬的四泉聖嘉祿教堂(San Carlo alle Quattro Fontane,1646)的曲線造形所啟發,塞拉的作品由一系列熱軋的鋼牆所組成,鋼牆接連形成時窄時寬的通道──形成由數個組件組合而成的巨大鋼材結構,其在靈感、尺寸與沉浸感方面,事實上都具有建築性。觀者無法看見這些曲折蜿蜒的鋼板的整體形體,對他們而言,在其中穿越移動的經驗是易於迷失方向的,同時也令人驚嘆不已。這些壯觀曲折的鋼板,其表面已經過噴沙處理,然後置放8到10年的時間而形成薄層的鐵銹,當觀者走入其間的通道,將因而顯得渺小。由於我們不知道作品將引導我們前往何處,一種不穩定感將加重我們的時空經驗,使我們都更能融入周遭肌理每分每秒的改變,以及每片鋼牆頂端之間細緻的空間建構。於此同時,移動在這些龐大結構所刻劃出來的負空間之中的經驗是輕盈的,幾乎是漂浮的:流動穿越過作品,就像是隨著一首激盪人心的音樂而起起落落。抑或是如藝術史學家哈爾‧福斯特(Hal Foster)所言,「這就好像你的身體變成它自己的雲霄飛車,並非上上下下的移動,而是轉了又轉。」
對徐永旭而言,塞拉的作品代表藝術成就的高峰。其形式上的作用及影響與徐永旭先前曾親身遭遇的任何事物都迥然不同。然而,這也令他極度焦慮,更加意識到他自己的創作媒材所帶來的挑戰。 他決定放棄一切而追尋藝術的決定是否將一無所成?黏土是否會自我抑制而影響此種工業製造物質的尺寸與壯觀?長久以來都與手工藝及實用主義聯想在一起的陶瓷,如何作為裝置形式而鼓舞觀者並激發感官與經驗上的感受?即使他得以黏土達成類似的傑出美學效應,身為台灣陶藝家的他,能否走出像塞拉這類藝術家或是歐美藝術規範下的其他泰斗的影子?
讚頌陰影
當徐永旭回到台灣之後,他開始徹底改變作品的尺寸與結構,並且很快發現他不須採取新的技法或工業製造方式來開拓他的雕塑的空間與經驗表現。相對於此,徐永旭轉向黏土製作最基礎的方式之一,此種方式在世界許多地方的陶器製作都被運用達千年之久。徐永旭此一創作上的轉變的最早例子之一是作品《2006-1》[圖7 – 2006-1],這也是他取得台南藝術大學美術碩士學位的畢業製作。徐永旭在平坦的平面上創作,先做出一細條黏土,然後在地上將其塑模成鬆散的卵形,高2公尺以上,寬約半公尺。他繼續在這基礎之上再圈上28條黏土,以手指將每一圈壓在一起,並在建構時測試此結構的張力限度。結果是製做出不可思議的細薄、搖擺狀的卵形牆體,其上有著不規則形的大洞,顯示他的手指在處理過程中穿破黏土的跡象。作品的表面再度完全佈滿藝術家的手指與雙手留下的痕跡,那是他處理每個黏土圈條的過程,以重複的姿勢揉捏、按壓黏土條而使其交織在一起,形似某種粗製的紡織品,或甚至是向塞拉點頭致意而展現出生銹鋼材的模樣。作品一經燒製之後,以其垂直軸矗立著,壯觀的呈現在觀者面前。
在數個月的過程中,徐永旭回到他的工作室,對黏土的不同成分進行無數次的實驗──將黏土混入沙子、紙與其他礦物及顏料,期望將黏土的彈性、吸收力、耐久性、強度最大化。在此段時期,徐永旭承受無數次的挫敗。由於每件作品都是整體燒製,這些雕塑特別容易在窯中崩毀。雖然擀壓、圈製、按壓黏土而成為這些龐大形體需要數小時──甚至數日──的體力耗費,但其滅失可能只是幾秒鐘的事。雖然持久性的概念經常都只單純歸屬於製作過程,然而這應該也要擴充至藝術家接納失敗的能力,藝術家必須能重拾作品而從頭做起。
2007年12月,徐永旭在其出生城市的高雄市立美術館舉辦首次個展,展名為《黏土劇場》,展覽令人印象深刻,共展出25件以泥條盤築成形法(coil building)所製作的抽象雕塑新作。此展預告了他創作的新方向。除了上述如生銹及燒焦般的赭色調作品之外,徐永旭也創作一系列黑曜石橢圓形作品,像是奇特的外星飛行器或大門,其表面暗淡地閃爍著,有如從燒焦的外星殞石粗製而成。[圖8a及b–黏土劇場裝置照片] 觀者受邀漫遊於此小型而具深淺色澤的雕塑森林之中,體驗矛盾的情緒感受。有些人會覺得這些雕塑的礦石感令人感到奇特的平靜,甚至可能感到被迫走入這些幾乎是人體尺寸的包覆物的空間之中,就像在洞穴或巢穴之內。其他人則是在面對其穿孔表面的肌理複雜性時,也就是在面對斑駁皺摺而有如某些外星生命體的厚實獸皮時,可能立即感到退縮畏懼。無論如何,此作品都能使其存在「令人有所感受」。
此展的展名也許也是在向徐永旭於參觀迪亞比肯美術館(Dia Beacon)時所看到的極簡主義與後極簡主義裝置點頭致意,因為它可以被看作是在參考一篇探討此類作品所造成的情動(affect)並激起大量藝術史論戰的重要文章。1967年,美國藝術史學家麥可‧弗雷德(Michael Fried,生於1939)對唐納德‧賈德(Donald Judd,1928-1994)及羅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1931-2018)等藝術家的作品進行評論,探討其「劇場性」(theatricality)──他們的作品透過其存在的單純物質性,或是「物性」(objecthood),而自覺地邀請觀者參與其中的概念。對弗雷德而言,物性不同於藝術,因為當人們站在藝術品之前時,「短暫的一刻將足夠長久而可使其看見一切,體驗整個作品的深度與全部而對其永遠信服。」 極簡主義物件對此清高而絕對的看法所提出的挑戰是轉而強調觀者在遇見作品時的身體經驗,也因而違反藝術自主中的類神聖現代主義信條。依極簡主義雕塑家莫里斯所言,「當某人從多重位置且在各種光線與空間脈絡的條件下理解物件時,他自己將建立起關係,並從而更加有所領會。」 觀者並非在單一時刻體驗作品,而是與作品進行對話與身體互動,並因而開啟一段時間,在此時間中,他們遊走於展場空間中,從不同的角度及不同的光線條件下觀看作品。
不須多言的是,如此的條件是受到相對控制的,是在藝廊的「白盒子」或博物館空間的清高環境之中,在此觀者會因應該機構的禮儀與限制而調整他們的行為。然而,在2009與2010年,徐永旭將其作品推向更廣泛的大眾,分別在台北當代藝術館與台北信義區展出戶外裝置[圖9a及b – 2009-59及2010-藝術在山左右01]。雖然大部分徐永旭的雕塑都相當巨大,而且可以忍受波動的天氣狀況所造成的磨損,但這些高聳的橢圓雕塑得以耐受可能來自公眾身體互動的能力也受到某些關注。相對於限制及監督公眾的行為而對作品加以警戒,或是在作品周圍放置標誌以警告可能產生的風險,徐永旭採取較為細緻而溫和的方式,勸導觀者在裝置周圍移動時當心留意。為此,他在每件較高的雕塑周圍的草坪上放置數百件較小的環形白瓷。這密集的微小雕塑就像是公眾道路與較脆弱、高聳作品之間的天然屏障,不會因為明顯的禁止與限制措施而模糊此裝置的美感經驗。觀者仍可接近雕塑並與其互動,但這些無數的細緻、弧形的較小物件的存在默默地提醒了大眾作品所使用的媒材具有脆弱性。此件作品特有非凡,──不只是美學上,而且是因為作品顯示藝術家相信大眾能自己與這些物件互動,並且是在那些機構的精英庇護空間之外。
雖然徐永旭是透過此種大型抽象陶瓷裝置來帶動觀者的首位台灣藝術家,有關藝術的現象學與經驗可能性的質疑自1980年代以來就已成為台灣藝評的主題。1984年及1985年,二項實驗性的展覽在台北春之藝廊舉行,展名分別為《異度空間》與《超度空間》,展出林壽宇(1933-2011)、莊普(生於1947年)、賴純純(生於1953年)等藝術家的現地裝置作品,他們將日常與工業物質佈滿於藝廊空間,期望觀者在與藝術相遇時能被細心地帶動與擾動。林壽宇獲得著名的《1985年中國現代雕塑展》首獎,該展是由推展現當代藝術的首要官方機構台北市立美術館所舉辦。
當時的館長蘇瑞屏在展覽專輯的序文中稱讚這些後極簡主義的台灣藝術家的作品,認為他們「精湛的技法與巧思的設計」是為了「透過不同材質的研究而在多重空間中探索更多的可能性」 評審之一的呂清夫更察覺在如此狀況下,「作品的尺寸巨大擴充(……)同時,作品成為與觀眾同在。觀眾得以進入作品的空間而成為作品的一部分;作品可延伸進入觀眾的生活空間並成為環境的一部分。」 然而,呂清夫更進一步辯稱林壽宇的作品代表一種中國特有的感受,其與停滯不前的西方全然相反:「展示台與畫框是西方沙龍藝術及『象牙塔』的產物。現代的[台灣]藝術試圖將作品從這些限制中解放出來。」 呂清夫並繼續以道家與佛家的哲學準則來描述台灣後極簡主義藝術家的作品,試圖說明這些創作的特色在於顯示新的「中國現代性」,具有明顯的反西方意涵。
藝術史學者兼策展人菲力克斯‧索博(Felix Schoeber)辯稱新設立的台北市立美術館積極促進這些實驗性的創作,啟動一個「現代藝術重新國有化的計畫,其牽涉到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的各個階層:學院教授、博物館行政人員、專業媒體,尤其是藝術雜誌,最後但並非最不重要的階層則是以民族主義詞彙來框架作品的藝術家本身。」 事實上,自20世紀以來,在亞洲許多地方,此種區別於西方藝術史霸權框架的本土實踐的反動訴求已成為評論的關注,尤其是在社會政治不確定的時刻,這促使評論重新評估何者首先構成「現代性」與「現代主義」。
在一篇撰寫於1933年──福西永上述書籍的前一年──名為《讚頌陰影》(譯註:中文譯名多為《陰翳禮讚》)的引人聯想的短文中,日本作家谷崎潤一郎(1886-1965)議論日本執迷於歐洲啟蒙的合理化原則,歐洲啟蒙曾經主導先前的明治時代(1868-1912)。和許多人一樣,谷崎察覺西方具有現代性、科技與進步的卓越象徵即是光線本身。就如他所述:
……先進的西方人總是堅決改善他們的生活狀況。從蠟燭到油燈,油燈到媒氣燈,煤氣燈到電燈──他們對於光線更加明亮的需求從未停止,即使是微不足道的陰影,他們也不遺餘力加以消滅(……)我們東方人則傾向安身於我們所處的現狀,滿足於事物本身(……)如果光線不足,就讓光線不足;我們會沉浸在陰暗中,並在該處發現其特有的美感。
谷崎在其文章中列舉許多例子,說明陰影如何成為「東方」美感經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舉出一些現象及其影響,從建築與摺紙到能劇與陶藝。就如他所見,日本對於暗淡、多變、捉摸不定的陰影的欣賞應被讚頌為一種本土固有的感受形式,同時也是對於西方殖民主義的科技與軍國主義攻擊的無聲抵抗,而西方殖民主義正對日本自己壯大中的擴張主義野心有著具有說服力的意識形態上的影響。
雖然谷崎的文章預見日本的帝國主義,但該文因為察覺「自我東方主義」而受到批評,同時也因其設定了東方與西方、傳統與進步的二元對立──儘管這樣的看法掩蓋了谷崎以輕鬆的諷刺語調處理這些沉重的跨文化比較的趣味性。事實上,谷崎的文章可以解讀為對於著名的柏拉圖洞穴寓言的諷刺回應,柏拉圖的洞穴是經常被引用的「西方」藝術史術語,用以隱喻意象的欺騙與錯誤的意識。 雖然有其觀察上的瑕疵,但此文章強調殖民主義事業的基本「摩尼教譫妄」(Manichean delirium),其近期被後殖民主義思想家轉移為一種抵抗的策略。自1960年代晚期起,馬提尼克島的文化理論家兼詩人艾德瓦德‧葛里桑特(Édouard Glissant,1928–2011)捍衛「不透明權」(right to opacity),此項舉動頗為聞名。就如他對此權力激動地讚揚道:「在透明性的世界性傳播與西方思想的投射中存在著不公正。為何我們評估人們時必須以西方提出的概念透明性做為評判的尺度?就我而言,一個人具有不想透明的權力。」 這令人想起前文引用的瓊安‧基的文章,她質疑:「當人人都只想知道你來自何處之時,為何還要在形式的問題上花費心思?」對非西方藝術家而言,亟欲依照自己的主張而成就最大的能見度──在不同的多焦光線下最後被看見、認可與讚揚──是至為重要的,如此而能全然走出主導的歐美規範的陰影或其他大一統的架構。同時,不透明的權力──某人不會覺得被壓迫或逼迫去透過其藝術而揭示其特有的種族、文化、社會政治承載,也因而不會造成自我與他人、中心與邊緣之間顯而易見的界線──是必須維護的一項權力。在台灣──一個自1700年代晚期以來即存在於許多殖民產業陰影之下的國家──的脈絡下,葛里桑特具政治意味的敘述特別能獲得共鳴。
以光織界
在一份名為《以台灣陶藝映射台灣歷史與其國家文化轉變》的著作中,梅豪方(Frank Muyard)提出:如果國家可以被視為歷史的「意外」,也就是特殊脈絡與事件的結果,則台灣陶藝的發展便「也是一種歷史意外」及「強烈反映社會歷史事件的歷史結果,這些事件使此島嶼轉變為我們今日所見的21世紀的台灣。」 事實上,陶藝發展,尤其是地方性的,無法輕易與國家、文化、藝術上的身分認同問題加以分割。畢竟,至少自18世紀以來,瓷器──最受珍視的陶瓷──就在英語系世界被稱為「China」(譯註:英語中「China」為中國,亦指瓷器)。 在台灣的脈絡中,此材質對於龐大中國文化的象徵性聯想至少可說是有問題的,因為在這多元種族的島嶼上上演著政治鬥爭,僅僅在上個世紀至少就存在三種民族主義──日本、中國、台灣。
梅豪方的研究聚焦於17世紀以來陶瓷生產的不同時期如何與更廣泛的地緣政治及經濟事件密不可分。在此歷史軌跡中有一較為近期的例子,實用性、中低價值的外銷陶瓷的大量生產是一項興盛的產業,在台灣自1950年代至1970年代受到政府的支持,但此情況逐漸轉移至中國大陸,就從其自1980年代對國外貿易與投資重新開放門戶以來。當然並非只有此項產業如此,由於工廠關閉與失業情形,造成了許多社會及經濟上的擔憂。
儘管如此,此項製造業在設備及材質上所建立起的技術知識與供應網絡為台灣「現代陶藝」的發展開路,使其成為有別於大量生產的實用器皿的一種自主發展現象。1980年代,中產階級的崛起與解嚴所帶來的更巨大的國際性影響,不僅促進如前所述的當代、實驗性、前衛的創作,而且也可見到官辦陶藝比賽與展覽的增加。 梅豪方辯稱,自1990年代以來,「聚焦於本土文化和身分認同,以及此項職業國際化的聯合效應(……)加速了本土陶藝的『台灣化』及其成為新的『國家的』藝術形式的轉變。」 陶藝的國家背書與制度化因鶯歌陶瓷博物館的成立而更為鞏固,該館於2000年11月開館,成為台灣首間縣立級的專項博物館。
在1980年代與1990年代,陶藝成為自主藝術形式一事獲得了更大的支持與關注,雖然此事無庸置疑地有助於許多藝術家以此媒材進行創作,包括徐永旭,但不能說徐永旭的創作體現了「國家形式」。反之,他致力突破「台灣陶瓷」風格上的傳統窠臼,力求跨歷史與跨文化的美學表現,與本土及全球的藝術史與理論潮流對話,聚焦於時間性、物質性、創作行為、藝術如何影響觀者等更廣泛的問題,其方式可視為有效地「促進可能分占世界兩極的藝術品之間的對話。」
徐永旭的跨國感知對其出生地高雄的特殊地區性的闡述更勝於其所反映出的同質性「國家」處境,此說法是值得商榷的。此地區的歷史特別豐富,至少可追溯至新石器時代,位於南部兩岸的鳳鼻頭文化(4500-2000 BCE)考古遺址可以為證,其在日本殖民時期於高雄林園區出土,以其紅色細繩紋陶器與石器農耕工具而聞名。 此種繩紋陶器發現於台灣、中國東南部、越南北部的事實成為激烈辯論的根源。考古學家威廉‧索爾海姆(Wilheilm Solheim)的論述頗為知名,他辯稱此分佈型態指出他所謂的「島民海洋貿易網絡」(Nusanto Maritime Trading Network)的文化分佈,該網絡自大約西元前5000年起在此地區的以海洋為生的南島民族間發展,索爾海姆因而更加強調了台灣與更廣大的泛亞洲文化體之間的原住民連結。
台灣的陶瓷大可成為台灣歷史與其國家及文化轉變的一面「鏡子」,但我們從鏡中所見卻難以反映真實生活。有鑑於其表面如何折射光線及其鏡面的形狀與質地,一面鏡子可以使我們所見的世界變形,或使我們從不同的角度與視點觀看事物,就如同從後視鏡或鏡室觀看一樣。
徐永旭是在其學習養成時期經歷過動盪的戒嚴「白色恐怖」的藝術家,對他而言,藝術必須傳遞直接的政治訊息或表現「國家」特色的概念是令人反感的。 這並不表示他只是堅守著「為藝術而藝術」的舊口號,而是對他來說,藝術及藝術創作的經驗不應該帶著世界的重量。這引人思索徐永旭作品的「輕」與無以名狀的佛教概念的「空」之間的關係,就如心經中的名言:「形無異於空,空無異於形。形即是空,空即是形。情感、知覺、意志、意識皆如是。」 然而,單純以東方哲學角度來思考徐永旭的創作將再度落入東西方二元論的風險,這對其作品跨文化的要旨並不公允。
此處再次回到谷崎的文章是有所幫助的,可以顯示徐永旭創作中曖昧不明的張力。當谷崎於1930年代早期撰寫該文之時,台灣成為日本殖民地已約莫20年,而且將一直持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很明顯的是,他在整篇文章中所使用的專有名詞「我們東方人」──不論諷刺與否──與其看起來相比,都顯得更不那麼黑白分明。然而,在對於陰影的讚頌中,谷崎所強調的絕非是黑暗與光線的兩極對立,而是其間的灰色陰影,他梳理出似乎是對立的兩者之間的共生關係。的確是因為有了光與影之間辯證性的交互作用,我們對於世界的理解與體會才能有其細微的差別與深度。
當專注於影子遊戲的詩性之時,谷崎和徐永旭一樣,也都聚焦於阻礙光線前進的日常物件、肌理與形體的默然存在,令我們質疑原先是清楚定義的、獨有的、自主的物件的穩固性與確定性。畢竟,影子的外觀是變幻莫測的,變換的因素從廣袤的大氣到極其細微之物:起伏不定的天氣狀況;我們建立及收集在我們周遭的物件的存在、形狀與物質性;與這些短暫而客觀有關的個人視角與位置。所有這些細微的變化就如音樂一般,以無以數計的不同方式將這世界導入光明之境。
1. Rosalind Krauss, ‘Richard Serra/Sculpture’ Richard Serra/Sculpture. ed. Rosalind Krauss, (New York: Museum of Modern Art) 1986, p 16.
2. Krauss, p 16.
3. 例如,可參見Jill H. Casid and Aruna D’Souza. Eds. Art History in the Wake of the Global Tur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及Hans Belting, et al. The Global Contemporary and the Rise of New Art World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3.
4. 參見 Wei Chu-Chiun, ‘From National Art to Critical Globalism’ Third Text Vol 27, Issue 4: 2013, pp 470-484; 及Tsai, Hong-Ming ‘Patchwork memory – mending the pieces’ in Taipei Biennial: The Quest for Identity. Exh Cat. (Taipei: Taipei Fine Art Museum) 1996, pp. 22-43.
5. 參見 Lu Pei-Yi, ‘Three Approaches to Socially-Engaged Art in Taiwan’ Yishu: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15, no 6, 2016, pp 91-101.
6. 有關這些發展更詳盡的狀況,請參見Julian Stallabrass, Art Incorporated. (London:Verso) 2004.
7. Partha Mitter 對這些發展提供了具說服力的討論,參見Partha Mitter, ‘Modern Global Art and its Discontents’ in Decentring the Avant-garde (Leiden: Brill) 2014.
8. Joan Kee. ‘Form in the service of the global’, Contemporary Art: 1989 to the Present eds, Alexander Dumbadze & Suzanne Hudson (Oxford: Wiley Blackwell) 2013, p 98.
9. Liao Jen-I. ‘From Lowly Dust to the Grandeur of the Universe – The Aesthetic Significance of Hsu Yunghsu’s Clay Sculptures’ in Becoming. Refrain: Hsu Yunghsu Solo Exhibition. (Taipei: Tina Keng Gallery) 2012. Pp 97-129.
10. Hsu Yung-hsu, Transcending Boundaries.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Master’s Dissertation. [DATE] 引述於 Sophia S.T. Wen, ‘Travelling through Emptiness – Hsu Yung-hsu’s Minimalist Expressions’ in Hsu Yung-hsu: Theatre of Clay Exh. Cat (Kaohsiung: Kaohsiung Museum of Fine Arts) 2007, pp 12-17, p 13.
11. 對作者的訪談,台南,2019年5月15日。
12. Tim Ingold, Making: Anthropology, Archaeology, Art and Architecture (2013). p 94
13. Glenn R. Brown, ‘Invention, Interaction and the Will to Preserve’ Ceramics Research Centre: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可見於網站:https://cream.ac.uk/ceramics-research-centre-uk/essay-series/contemporary-essay-5-glen-r-brown/ Accessed 20/6/19.
14. Yves Alain Bois and Rosalind Kraus, Formless: A User’s Guid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97.
15. Liao Jen-I, 2012, p 98.
16. Henri Focillon, The Life of Forms in Art trans. Charles B Hogan and George Kubler (New York: Zone Books) 1989, p 170.
17. 福西永的學生,美國籍的George Kubler,也繼續撰寫一冊《The Shape of Time》,其對Robert Smithson、Fred Sandback等極簡主義藝術家有深刻的影響。參見Pamela M Lee, ‘Ultramoderne, or, how George Kubler stole the time in 1960s Art’ in Chronotopia: On time in the art of the 1960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4.
18. Hal Foster, ‘Torques and toruses’ in Richard Serra: Torqued Spirals, Toruses and Spheres. (New York: Gagosian Gallery), 2001, p 9.
19. 對作者的訪談,台南,2019年5月15日。
20. Fried, Michael. Art and Objecthood: Essays and Review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P 167
21. Robert Morris, ‘Notes on Sculpture Part 3’ Artforum 1967, Vol 5, no 10, pp 24-29, p 25.
22. Su Rui-ping, ‘Preface’ in 1985 Exhibi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culptur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pei Fine Arts Museum exh Cat, (Taipei: TFAM), 1985, p 2.
23. Lu Chin-fu, ‘Farewell pedestal, back to the public square,’ in 1985 Exhibi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culptur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pei Fine Arts Museum exh Cat, (Taipei: TFAM), 1985, p 10.
24. Lu Chin-fu, 1985, p 10.
25. Felix Schoeber. Modernity, nationalism and global marginalisation: representing the nation in contemporary Taiwanese art exhibitions.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2014. Pp 103-4.
26. Junichiro Tanizaki, In Praise of Shadows trans. Thomas J Harper, (Stony Brooks CT: Leete Island Books) 1977, p 31.
27. 參見Viktor Stoichita, A Short History of the Shadow (London: Reaktion Press) 1997.
28. Manthia Diawara, ‘Conversation with Edouard Glissant aboard the Queen Mary II’ (August 2009) 可見於網站:https://www.liverpool.ac.uk/media/livacuk/csis-2/blackatlantic/research/Diawara_text_defined.pdf (accessed 1/11/2019)
29. Frank Muyard, ‘Taiwan Ceramics as a Mirror of Taiwan History and its National Culture Shift’ in Objects, Heritage and Cultural Identity, Ed. Frank Muyard, Liang-Kai Chou and Serge Dreyer (Taipei: Taiwan Historica) 2009, p 391.
30. 參見Chen, Hsin-hsiung. Taoci Taiwan [Taiwan’s Ceramics]. (Taichung: Chen Hsing Press) 2003.
31. 參見Hsieh, Tung-shan, Taiwan xiandai taoyi fazhanshi [A history of Modern Taiwanese Ceramics] (Taipei: Artist Press) 2005.
32. Muyard, 2009, p 405.
33. Kee, 2013, p 103.
34. 參見 Jiao Tianlong, The Neolithic of Southeast China: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Regional Interaction on the Coast’ (Amhurst NY: Cambria Press) 2007, pp 101-102.
35. Solheim, Wilheim G, ‘Taiwan, coastal South China and northern Viet Nam and the Nusanto Matirime Trading Network.’ 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 2(1-2), 2000 pp 273-284; 及Solheim, Wilheim G, ‘’Southeast Asian earthenware pottery and its spread’, Earthenware in Southeast Asia: 1-21.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2003.
36. 對作者的訪談,台南,2019年5月15日。
37. 參見Donald S. Lopez, Elaborations on Emptiness: Uses of the Heart Sutr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