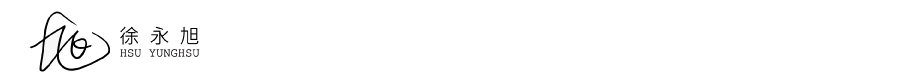邊界Boundary-徐永旭個展
邊界Boundary-徐永旭個展
2022.4.23(六)~2022.6.11(六)
臺南市中西區忠義路二段186號
弎畫廊
關於「徐永旭個展-邊界Boundary」
文|沈裕融 寫於展覽之前
面對藝術家的書寫者,十分像是置身於叢林中追逐野獸的追蹤師。野獸的行動路徑,構成了一座由他們自身所築造的迷宮(labyrinth) 。若將藝術家喻為代達羅斯(Daedalus),即迷宮(同時將自己困限於其中)精湛的建設者,那麼協同觀者的書寫者或許就成了嘗試走入迷宮、肯定迷宮,並意願深入(而非逃離)其中的忒修斯(Theseus)。這樣一來,誰是我們的阿里阿特涅(Ariadne)——那將線團交給我們,指引我們走入迷宮而不至迷失的引路者?
面對此種狀況,伊卡洛斯(Icarus)嘗試以垂直超越的方式逃離迷宮的慘敗故事已為我們指明此路不可循。我們只能藉由反覆仔細檢索所有的痕跡,左右打探消息,以此找尋線頭的所在。即便我能夠透過對談的過程尋訪藝術家徐永旭,但「徐永旭」毋寧是一道由展覽「徐永旭個展-邊界Boundary」再次拋擲出的謎團。本文的書寫正是從這些過往文字、影像紀錄與作品的反覆查考中,找到了面對此一謎團的可能線索:陳黎恆青於2015年所拍攝的《HELiOS旭HiOK:徐永旭個展》影片中,出現了這樣一個短焦段的特寫畫面,而相似的鏡頭處理同樣也出現在邱勤庭2019年為徐永旭於高美館的展覽《以光織界:徐永旭的藝術世界》裡,兩者皆不謀而合地拍攝了捆繞、層疊著肌內效貼布(KT Tape)的拇指、食指與中指的手,以某種「手勢」(gesture)的運動,被懸置於景框中。而那些錯綜於皮膚表層的藍色肌內效貼(即起伏於手部迂迴纏繞的線),似乎成了指引我們走入「徐永旭」這座迷宮的阿里阿德涅之線。它們不僅引導我們將目光指向在無盡重複中的疲憊身體,更將焦點指向了使一切行動與痕跡成為可能的技術之手。
首先我想指出的,是這些纏繞著的線與手之間的複雜關係。如果說徐永旭反覆以手指按壓的方式,將每一當下的過程一格、一格地烙印於陶土上,使其呈顯為具有深度的可見痕跡之書寫,是一種外化的內在書寫;那麼這些纏繞的肌內效貼之線的貼紮或可被視為起於對筋肉之拉扯耗損的覺察後的書寫,則是一種內化的外在書寫。這些亮藍色的線條十分像是重點劃記(highlight),邀請我們在面對書寫(即一件件作品)時,同時也意識到對書寫行動的書寫。但,這些線條想要將我們引導向何處?
徐永旭曾在2006年左右提出他對於「反陶」(anti-ceramics)的思考。他談到,陶瓷的材質在人類既存的思維中一直與「堅硬易碎」連結再一起,而這正是他的反陶行動中,藉由「大」挑戰工具、材料與技術的限制性,藉由「薄」抽除大的結構性,直面材料本身物理性的變化和重力的雙重應力下的影響。就此來看,「堅硬」與「易碎」指向的,應是「陶/器」,而不是「陶/土」:前者只是作為對象(object)的物,是被人從自然中抽離、捕捉、孤立出來的認識對象,並服膺於人的有用性價值之物,而此種意義下的物,是受格的物,一種被支配並服從於主體的否定之物。一旦人以此方式面對(被支配的)物,人與自然,或者說人與土的本然連結關係反而喪失了。故此,「反陶」並不是一種單純的否定,而是對於被否定之物的再否定;它所渴望的不再是認識(savoir)與擁有(avoir),而是要求恢復被切斷的連續性。
按照這樣的說法,「反陶」難道是要我們拒絕一切技術,否定使用價值,使我們回到自然主義的天真懷想嗎? 並非如此。原因不僅是不願,也不可能。一如史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對於艾比米修斯(Epimetheus)與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神話的思考,正因為艾比米修斯的過失,使人沒有被分配到如其他動物般的潛力(dunamneis),以至於需要靠普羅米修斯為人類偷竊技術來彌補這樣的缺失。技術成為人先天的義肢。而人之所以為人,也無法擺脫對技術的需求,因為人並非本然所是,而是在人化的過程當中成而為人的。問題不在於技術與自然的抉擇,而是如何協調兩者使其共生。而這裡的共生所指的,也不僅只是人與技術物的共生,更同時指向作為技術物的身體與人之間的共生關係。
徐永旭提到,在創作的過程中,除了切土器,他幾乎不使用任何額外的工具,而僅只憑藉自己的雙手。 佈滿劃記的手(以及為了支撐、舒緩筋肉而在勞作中殘破不堪的肌內效貼)是不言而喻的明證。但除了切土器,難道在徐永旭的創作中就不存在著工具嗎?並非如此。只是這個「工具」在上手性(Zuhandenheit)中隱蔽自身而被遺忘。唯獨在「工具」失效、損毀而不合用時,才呈現為手前性(Vorhandenheit)。這裡的「工具」——就是手(特別是被劃記的手,那銀幕中那靈活轉動的大拇指,它自由地與食指、中指、無名指、小指相互鉗扣,碰觸著)。人類的手相當於萬用的工具,它之所以能夠握、按、扭、拉、捏、擠、塑等數不勝數的姿勢,與人類在演化中形成那異常靈活的對生拇指(opposable thumb)息息相關。大拇指可被視為人類演化的重要標記,正因為這一演化結果,人類的手不再像黑猩猩那樣為在樹叢間移動而抓握樹枝甩盪,而是因著拇指屈肌與其他三條肌肉的協作,人才能更能精準地施力於手指進行捏握,乃至使用器物等精密工作。
故此,我們初步明白,劃記的線提供了對反陶之思的進一步思考。一方面,徐永旭透過「反陶」提出使「陶/器」脫離物世界秩序的有用性,同時也讓技術的操持者得以從這一功利性的迴路中得以解放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徐永旭更將「手」(特別是透過反覆的拇指按壓以及與其他指頭之間的協作關係)從目的性的指向運動中,回返於對自身的質問。正如龔卓軍所指出,若將徐永旭的創作視同肉身苦行,實是「過度強調了個體逾越能量,這時候,作品就變成藝術家修行後的殘留物,被忽略了自身的存在理由」 。這裡提到的「自身」,或許不是作品,也不是作者,而是藉由那被劃記的手所指向的技術存在。手不僅操作工具,手同時也是完美與肉身整合(所以被遺忘)的工具。手與物的脫鉤,使手暫得以被擱置。是什麼構成這種獨特技術(手)的存在?是「手勢」。手可被視為倫理性的技術工具,他不只使用,更連結;不只佔有,更照料。手勢是手與遭逢世界共構的無聲言說。
徐永旭時常談到2005年在美國紐約羅徹斯特工藝家學校(RIT)的駐校經驗。在身體與精神極度倦怠的狀況下,他對自身到新環境如何開始創作感到焦慮,於是順手抓了一把泥土,開始不斷地按壓,最後形成一個個極薄,彷彿船形的杯狀物小形體。藉由這種反覆按壓與捏塑的行為中,徐永旭嘗試不去思考行動的意向性指向何處,而是著眼於這一身體先行的行動本身。徐永旭的這一身體運動,與誕生於網路世代的拇指姑娘(Petite Poucette)有著巧妙的對話關係。按照塞荷(Michel Serres)的觀點,這一現象意味著知識關係的決定性轉變,即是說,借用聖德尼(Saint Denis)斷頭的強烈意象作為比喻,如今我們的頭顱已經離開了原先的優越位置:知識被外置化為某物(從蘇美人的黏土版、古騰堡的印刷機,到電腦螢幕,再到互動感測裝置)。每一次知識外化的技術革命,都再一次改變人保存、調度知識的連結方式。如今,不再需要詩歌的傳唱,不再是文字的書寫,而是透過手勢,一切訊息得以被展示、傳遞、召喚前來。徐永旭讓意向性的行動回到純粹的手勢,因為手勢將成為記憶於身體的(元)語言,而手印就是以此展開的(元)文字。
值得注意的是,徐永旭這些手勢並不是在建構視覺之外在性,而是回應聽覺之內在性。長年彈奏古箏的手勢(比如指法中的托、劈、勾、剔、挑、抹、打、提、搖指、揉弦、大撮、小撮等技法),所欲摸索的乃是在弦與弦、弦與指、指與音、音與意之間的境。他提到,雖然很早就決定開始學習古箏,但一直到遇見第三個老師,才真正對中國傳統音樂的「律學」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音與音之間築起的旋律、節奏不在於對抗,而在於和諧共構。「樂」所關乎的非僅是個體的心志,而更擴及對存在整體之感受 ;非指向「物」的技藝展現,而更是關乎以「人」為核心達至之共體存在 的終極性。
徐永旭曾提到在美國駐村時,偶然看到理查・塞拉(Richard Serra)、法蘭克・桑巴克(Frank Sanback)、弗雷德・仙貝克(Fred Sandback)等低限藝術家對材質、空間、身體的處理方式而感到衝擊。然而,低限主義(Minimalism)雕塑一方面提供了徐永旭對序列性、重複性以及場域的思考,但與此同時,這種對於作品物性的強化,以及對於作者情感的過份抽離,與前述「樂」的東方美學的思考自然產生了有待消解的矛盾與衝突。對此,徐永旭嘗試採取的策略並非抉擇(選擇任一者都意味著排除),而是調解(modulation):他必須將自身從創作主體化身為媒介物(medium)。如此,我們或可明白何謂徐永旭意義下的「邊界」。邊界即媒介(media) 。
那纏繞著亮藍色線條的劃記之手並不隸屬於「一具(封閉的)身體」,而手中揉製的土也不是「一個(穩定的)媒材」,那充斥於這兩者背景的更不是「一個(真空的)空間」。所有的邊界懸浮搖晃著。環境是浮動的,泥土是浮動的,濕度是浮動的,氣壓也是浮動的,而身處在這之中的人也是浮動的。 從土製成到乾燥經歷第一次收縮,在素燒、高溫燒製下經歷第二、三次的收縮,巨型作品經歷收縮如何能在土的拉扯中維持其穩定性而不崩塌,所仰賴的就不可能是絕對地控制,而只能是在所有歷程中對整體外在條件進行感知與預判 。土是媒介,身體是媒介,火是媒介,空氣是媒介,人亦是媒介。媒介保證兩者之間的溝通、協作與交流,所有的邊界都等待被瓦解、撕裂、跨越,然後彼此成全。正是在這樣的時刻,身土不二。
2022.4.23(六)~2022.6.11(六)
臺南市中西區忠義路二段186號
弎畫廊
關於「徐永旭個展-邊界Boundary」
文|沈裕融 寫於展覽之前
面對藝術家的書寫者,十分像是置身於叢林中追逐野獸的追蹤師。野獸的行動路徑,構成了一座由他們自身所築造的迷宮(labyrinth) 。若將藝術家喻為代達羅斯(Daedalus),即迷宮(同時將自己困限於其中)精湛的建設者,那麼協同觀者的書寫者或許就成了嘗試走入迷宮、肯定迷宮,並意願深入(而非逃離)其中的忒修斯(Theseus)。這樣一來,誰是我們的阿里阿特涅(Ariadne)——那將線團交給我們,指引我們走入迷宮而不至迷失的引路者?
面對此種狀況,伊卡洛斯(Icarus)嘗試以垂直超越的方式逃離迷宮的慘敗故事已為我們指明此路不可循。我們只能藉由反覆仔細檢索所有的痕跡,左右打探消息,以此找尋線頭的所在。即便我能夠透過對談的過程尋訪藝術家徐永旭,但「徐永旭」毋寧是一道由展覽「徐永旭個展-邊界Boundary」再次拋擲出的謎團。本文的書寫正是從這些過往文字、影像紀錄與作品的反覆查考中,找到了面對此一謎團的可能線索:陳黎恆青於2015年所拍攝的《HELiOS旭HiOK:徐永旭個展》影片中,出現了這樣一個短焦段的特寫畫面,而相似的鏡頭處理同樣也出現在邱勤庭2019年為徐永旭於高美館的展覽《以光織界:徐永旭的藝術世界》裡,兩者皆不謀而合地拍攝了捆繞、層疊著肌內效貼布(KT Tape)的拇指、食指與中指的手,以某種「手勢」(gesture)的運動,被懸置於景框中。而那些錯綜於皮膚表層的藍色肌內效貼(即起伏於手部迂迴纏繞的線),似乎成了指引我們走入「徐永旭」這座迷宮的阿里阿德涅之線。它們不僅引導我們將目光指向在無盡重複中的疲憊身體,更將焦點指向了使一切行動與痕跡成為可能的技術之手。
首先我想指出的,是這些纏繞著的線與手之間的複雜關係。如果說徐永旭反覆以手指按壓的方式,將每一當下的過程一格、一格地烙印於陶土上,使其呈顯為具有深度的可見痕跡之書寫,是一種外化的內在書寫;那麼這些纏繞的肌內效貼之線的貼紮或可被視為起於對筋肉之拉扯耗損的覺察後的書寫,則是一種內化的外在書寫。這些亮藍色的線條十分像是重點劃記(highlight),邀請我們在面對書寫(即一件件作品)時,同時也意識到對書寫行動的書寫。但,這些線條想要將我們引導向何處?
徐永旭曾在2006年左右提出他對於「反陶」(anti-ceramics)的思考。他談到,陶瓷的材質在人類既存的思維中一直與「堅硬易碎」連結再一起,而這正是他的反陶行動中,藉由「大」挑戰工具、材料與技術的限制性,藉由「薄」抽除大的結構性,直面材料本身物理性的變化和重力的雙重應力下的影響。就此來看,「堅硬」與「易碎」指向的,應是「陶/器」,而不是「陶/土」:前者只是作為對象(object)的物,是被人從自然中抽離、捕捉、孤立出來的認識對象,並服膺於人的有用性價值之物,而此種意義下的物,是受格的物,一種被支配並服從於主體的否定之物。一旦人以此方式面對(被支配的)物,人與自然,或者說人與土的本然連結關係反而喪失了。故此,「反陶」並不是一種單純的否定,而是對於被否定之物的再否定;它所渴望的不再是認識(savoir)與擁有(avoir),而是要求恢復被切斷的連續性。
按照這樣的說法,「反陶」難道是要我們拒絕一切技術,否定使用價值,使我們回到自然主義的天真懷想嗎? 並非如此。原因不僅是不願,也不可能。一如史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對於艾比米修斯(Epimetheus)與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神話的思考,正因為艾比米修斯的過失,使人沒有被分配到如其他動物般的潛力(dunamneis),以至於需要靠普羅米修斯為人類偷竊技術來彌補這樣的缺失。技術成為人先天的義肢。而人之所以為人,也無法擺脫對技術的需求,因為人並非本然所是,而是在人化的過程當中成而為人的。問題不在於技術與自然的抉擇,而是如何協調兩者使其共生。而這裡的共生所指的,也不僅只是人與技術物的共生,更同時指向作為技術物的身體與人之間的共生關係。
徐永旭提到,在創作的過程中,除了切土器,他幾乎不使用任何額外的工具,而僅只憑藉自己的雙手。 佈滿劃記的手(以及為了支撐、舒緩筋肉而在勞作中殘破不堪的肌內效貼)是不言而喻的明證。但除了切土器,難道在徐永旭的創作中就不存在著工具嗎?並非如此。只是這個「工具」在上手性(Zuhandenheit)中隱蔽自身而被遺忘。唯獨在「工具」失效、損毀而不合用時,才呈現為手前性(Vorhandenheit)。這裡的「工具」——就是手(特別是被劃記的手,那銀幕中那靈活轉動的大拇指,它自由地與食指、中指、無名指、小指相互鉗扣,碰觸著)。人類的手相當於萬用的工具,它之所以能夠握、按、扭、拉、捏、擠、塑等數不勝數的姿勢,與人類在演化中形成那異常靈活的對生拇指(opposable thumb)息息相關。大拇指可被視為人類演化的重要標記,正因為這一演化結果,人類的手不再像黑猩猩那樣為在樹叢間移動而抓握樹枝甩盪,而是因著拇指屈肌與其他三條肌肉的協作,人才能更能精準地施力於手指進行捏握,乃至使用器物等精密工作。
故此,我們初步明白,劃記的線提供了對反陶之思的進一步思考。一方面,徐永旭透過「反陶」提出使「陶/器」脫離物世界秩序的有用性,同時也讓技術的操持者得以從這一功利性的迴路中得以解放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徐永旭更將「手」(特別是透過反覆的拇指按壓以及與其他指頭之間的協作關係)從目的性的指向運動中,回返於對自身的質問。正如龔卓軍所指出,若將徐永旭的創作視同肉身苦行,實是「過度強調了個體逾越能量,這時候,作品就變成藝術家修行後的殘留物,被忽略了自身的存在理由」 。這裡提到的「自身」,或許不是作品,也不是作者,而是藉由那被劃記的手所指向的技術存在。手不僅操作工具,手同時也是完美與肉身整合(所以被遺忘)的工具。手與物的脫鉤,使手暫得以被擱置。是什麼構成這種獨特技術(手)的存在?是「手勢」。手可被視為倫理性的技術工具,他不只使用,更連結;不只佔有,更照料。手勢是手與遭逢世界共構的無聲言說。
徐永旭時常談到2005年在美國紐約羅徹斯特工藝家學校(RIT)的駐校經驗。在身體與精神極度倦怠的狀況下,他對自身到新環境如何開始創作感到焦慮,於是順手抓了一把泥土,開始不斷地按壓,最後形成一個個極薄,彷彿船形的杯狀物小形體。藉由這種反覆按壓與捏塑的行為中,徐永旭嘗試不去思考行動的意向性指向何處,而是著眼於這一身體先行的行動本身。徐永旭的這一身體運動,與誕生於網路世代的拇指姑娘(Petite Poucette)有著巧妙的對話關係。按照塞荷(Michel Serres)的觀點,這一現象意味著知識關係的決定性轉變,即是說,借用聖德尼(Saint Denis)斷頭的強烈意象作為比喻,如今我們的頭顱已經離開了原先的優越位置:知識被外置化為某物(從蘇美人的黏土版、古騰堡的印刷機,到電腦螢幕,再到互動感測裝置)。每一次知識外化的技術革命,都再一次改變人保存、調度知識的連結方式。如今,不再需要詩歌的傳唱,不再是文字的書寫,而是透過手勢,一切訊息得以被展示、傳遞、召喚前來。徐永旭讓意向性的行動回到純粹的手勢,因為手勢將成為記憶於身體的(元)語言,而手印就是以此展開的(元)文字。
值得注意的是,徐永旭這些手勢並不是在建構視覺之外在性,而是回應聽覺之內在性。長年彈奏古箏的手勢(比如指法中的托、劈、勾、剔、挑、抹、打、提、搖指、揉弦、大撮、小撮等技法),所欲摸索的乃是在弦與弦、弦與指、指與音、音與意之間的境。他提到,雖然很早就決定開始學習古箏,但一直到遇見第三個老師,才真正對中國傳統音樂的「律學」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音與音之間築起的旋律、節奏不在於對抗,而在於和諧共構。「樂」所關乎的非僅是個體的心志,而更擴及對存在整體之感受 ;非指向「物」的技藝展現,而更是關乎以「人」為核心達至之共體存在 的終極性。
徐永旭曾提到在美國駐村時,偶然看到理查・塞拉(Richard Serra)、法蘭克・桑巴克(Frank Sanback)、弗雷德・仙貝克(Fred Sandback)等低限藝術家對材質、空間、身體的處理方式而感到衝擊。然而,低限主義(Minimalism)雕塑一方面提供了徐永旭對序列性、重複性以及場域的思考,但與此同時,這種對於作品物性的強化,以及對於作者情感的過份抽離,與前述「樂」的東方美學的思考自然產生了有待消解的矛盾與衝突。對此,徐永旭嘗試採取的策略並非抉擇(選擇任一者都意味著排除),而是調解(modulation):他必須將自身從創作主體化身為媒介物(medium)。如此,我們或可明白何謂徐永旭意義下的「邊界」。邊界即媒介(media) 。
那纏繞著亮藍色線條的劃記之手並不隸屬於「一具(封閉的)身體」,而手中揉製的土也不是「一個(穩定的)媒材」,那充斥於這兩者背景的更不是「一個(真空的)空間」。所有的邊界懸浮搖晃著。環境是浮動的,泥土是浮動的,濕度是浮動的,氣壓也是浮動的,而身處在這之中的人也是浮動的。 從土製成到乾燥經歷第一次收縮,在素燒、高溫燒製下經歷第二、三次的收縮,巨型作品經歷收縮如何能在土的拉扯中維持其穩定性而不崩塌,所仰賴的就不可能是絕對地控制,而只能是在所有歷程中對整體外在條件進行感知與預判 。土是媒介,身體是媒介,火是媒介,空氣是媒介,人亦是媒介。媒介保證兩者之間的溝通、協作與交流,所有的邊界都等待被瓦解、撕裂、跨越,然後彼此成全。正是在這樣的時刻,身土不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