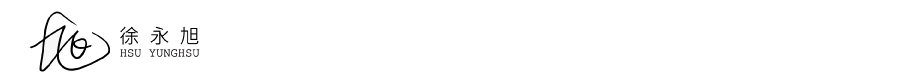人生逆轉學/藝術家徐永旭年過半百為陶藝淪貧窮 化人生風雨入作品
病痛讓他每個創作動作都很艱辛 卻內化成人生重要部分
藝術家徐永旭用大拇指在陶土依序按壓,每一指都留下一個凹陷,結結實實用身體在作品烙印下圖 案。外人看這些成果抽象美麗,不知他每一動作常忍著多年風濕性關節炎的痛楚;作品隨機發展的 人生逆轉學/藝術家徐永旭年過半百為 陶藝淪貧窮 化人生風雨入作品 優雅線條,更淬鍊自他人生的風風雨雨。 在徐永旭位於台南的500坪工作室,藝術家晃著一頭微亂的捲髮,淡淡說痛對他而言,已根本稀鬆 平常,「是我人生很重要的部分」。當痛已內化進身體太久,他已不感覺那是痛;人生中所有逆 境,於他也如此。
省下3個月午餐錢買考題本 拚上雄中
徐永旭原本想當運動員。家境貧寒的他,從小田徑和畫畫都出色,但田徑在「亞洲鐵人」楊傳廣揚 名的年代,才更有未來。參加田徑隊保送進初中時,他一心想躍進全國競賽前三名,好爭取台中一 中體育實驗班公費生名額、將來當國手,卻在初三一場選拔賽受傷夢碎。 緊急改考一般高中時,徐永旭自知從頭複習已來不及,尋思買模擬考題練習。深知家裡沒餘錢,他 只得騙媽媽便當蒸後有怪味、會反胃,求媽媽一天給他2元吃麵,再忍住飢餓只喝水,4天累積8元 買一本7元考題。苦練幾本考題下來,他考上第一志願高雄中學,代價是3個月沒吃午餐。
減輕家中負擔 公費師專、白天教小學晚上教古箏
家裡不可能供他念高中,徐永旭念了公費師專,一邊學起古箏,技藝成長速度和運動與畫畫同樣飛 快。師專畢業後,在牡羊座的拚勁加上養父母、還家裡房貸的經濟壓力下,他每日白天教小學、晚 上教古箏,還開了5場售票古箏獨奏會,「我是投入什麼,就要做到有舞台、有掌聲。」 沒日沒夜工作奔波10年,徐永旭身體亮起警訊。眼看家裡債務近還清,又有感古箏藝術境界有限, 他決定放下古箏,重拾油畫畫筆,陶藝世界卻在此時向他展開。
只剩3年就能退休 他為陶藝辭去小學教職
起初是有位小學同事邀他合夥開陶藝工作室,從未做過陶的徐永旭雖然覺得莫名其妙,還是答應。 有了工作室,他試著摸索做陶,失敗一陣後,不服輸的意志湧上來,他大量買書自學,整個人栽入 陶藝。 「我太太說,人家只是要你玩土,你卻是在玩命!」徐永旭說,當時他生活漸趨安定,雖然小學教 職薪水不高,至少有保障,他偏偏投入陶藝創作,一創作又想著要展出、拚舞台。他開始參加比賽,還首次參賽就入選,一路拚到1994年奪得台北市美展陶藝類首獎,兩年後就有畫 廊邀他個展,「路好像開出來了」。然而當展約愈來愈多,明明該為渴望的舞台做作品,卻卡在白 天仍得當小學老師,創作時間遠遠不夠。掙扎兩年,徐永旭決定辭去小學教職。 當時離合法退休只剩3年,但徐永旭不想再等。「那時我再也受不了了,我想做的是藝術創作!」 同為小學老師的學妹太太與他僵持一陣,最後讓步,接受丈夫走上全職藝術家之路。
畫廊銷售不如預期 決定開展上海市場
想像中平穩的藝術家之路,很快就現出顛簸真相。徐永旭說,他原本估計作品照之前的畫廊銷售成 績,每年穩定售出幾件,加上憑得獎招牌開班教學生,生活費應該沒問題。但他不久就發現,並非 每檔展覽都賣得出作品:他曾載了一大卡車作品去畫廊展,只賣掉一小件,55拆帳後拿到8000元; 學生量也不見得穩定。 2000年,徐永旭決定擴大藝術市場版圖。那年他應邀去韓國展覽演講,觸動他固定在兩地展覽售出 的模式:「台灣很小,如果我同時在國外展出,機會應該多一倍。」恰好中國也有展覽邀,最後他 在首爾和上海間,決定去上海。
為省錢犧牲生活品質 異鄉打拚萬分淒涼
原本期待的藝術路翻轉點,無奈急墜為人生低點。徐永旭說,到了異鄉,他才體會到單打獨鬥有多 辛苦,從買作品材料、做作品到在畫廊展出、銷售等,全都要一人完成,相關程序和台灣迥異,耗 掉大量精神。 更難受的是生活狀態。徐永旭說,上海又濕又冷,他為省錢,只能租沒暖氣的房,晚上睡覺時皮膚 露到被子外都會凍到痛;也是為省錢,他從馬路邊一餐人民幣5元,吃到巷子內一餐4元,再到彎進 去更小巷的3元。生活品質一路往下。最難熬的是孤獨。徐永旭說,他在2000年之前,在工作之餘可說足不離戶,看顧家裡老父母與妻子 小孩。突然獨走上海,狀況簡直像拋家棄子、離家出走,太太難免有埋怨。在每個濕冷的夜裡,他 望著窗外路燈照進房內玻璃窗,映著天寒結成的露水在窗上不斷流動,好像一幅會動的水墨畫,心 中淒涼萬分。
回台圓碩士夢 成全校最老學生
3年後,徐永旭終於返台,卻沒回家,而是直奔台南藝術大學圓碩士夢。當時他已近50歲,是全校 最老的學生。 「在那個年紀,那個狀態,口袋常常空空,真的壓力滿大……」徐永旭說,2000年離台時,他自知 不能讓太太負擔全家生活,就說好各自負責一個孩子學費生活費,來念書時亦然。眼見存款有限, 他不得不先告訴老師,自己可能沒法念完書就離開。2006年,徐永旭要做畢業製作卻沒錢,不得不向買過他作品的買家和朋友、同事募款,允諾之後以 作品回贈。2008年他做完高雄市美術館個展作品時,存款簿只剩幾萬元,「一個50幾歲、有家庭的 人,那心情有多焦慮?」 然而也正是徐永旭口中「最飄蕩的歲月」這幾年,讓他作品有了天翻地覆的改變。去上海那幾年看 似沒搞出什麼,但正是那段時間的狀態,逼他更深層地從過去作品只是表現外在世界,回到觀察自 己內心。他大量閱讀哲學,進而返台念碩士;並因碩士的思想震撼與親炙美國雕塑家Richard Serra 的巨大創作,重新思考什麼是只有陶這種材質才能表現。
陶土彷彿有靈性 紀錄他的一切
他思索,Serra的鋼雕是設計好後,交工廠製作,藝術家不在作品帶入任何身體情感;陶藝剛好相 反。「我要用陶土記錄我的身體,我的時間,我的狀態,我的情感,留下印記。」 早期古典具象造型、敘事為主的作品風格,徐永旭全數捨棄。他要徒手做只有陶土可以表現的作 品,讓泥土變成他創作唯一可能的媒材。他不畫草圖,不賦予造型任何意義,雖然大概可想像成品 形貌,但不限制過程中各種發展可能。每次做作品前,只先決定量體大小與大致手法,例如是要掛 牆壁或立體放置,形體又大約是條狀或片狀,之後雙手就開始與泥土隨機起舞。徐永旭示範:決定作品形體是片狀後,他用手捏出一層層弧狀。陶土軟,做到相當高度時容易塌, 此時順勢轉變陶土方向,陶土就不會塌下。所有的結構都是當下發展,連結出觀者眼中的造型。做 久了,徐永旭感覺,這些作品都是他與彷若有靈的陶土在同個狀態下一起成就。 然而這樣巨大的陶作做起來非常耗費體力,尤其徐永旭從1982年就罹患風濕性關節炎,每一運指常 痛入心扉。但長年痛下來,徐永旭感覺痛也是他人生的重要部分,就像他人生一路走來所有的難關 打擊,回頭看都只是過程。
500坪工作室「拚死拚活」維持 創作給足滿足感
近年徐永旭屢獲吳三連藝術獎等大獎,展覽也好評不斷。但徐永旭仍有困境:2009年設立的500坪 工作室維持成本極高,「拚死拚活」下來,大約就是賺到自己繼續創作。然而若不繼續工作室,他 就無法做這類巨大作品,也就無法得到滿足感。「我是需要舞台和掌聲的人,這些會更刺激我的創 作力量。」創作帶給他的幸福感也無法言喻。徐永旭說,他在生活中覺得最開心幸福的時刻,就是在工作室做 陶,以及晚上與太太一起跑步。過去人生的風雨,此刻早已平息,化為優美的作品,超脫所有的情 緒,不落言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