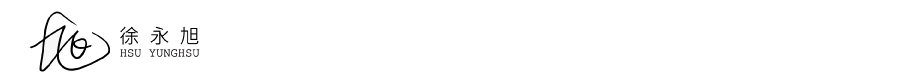存在與時間–徐永旭陶塑作品的生命觀
哲學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在著作《存在與時間》(Sein and Zeit)中,提出「此在」(Dasein)的概念,強調時間與存在的關係,認為事物或生命不是超越的主體,而是存在於世界之中、存在於時間中的「此在」;這個「此在」不能離開世間萬物而存在,而是與世界是相互構成的。從1985年成立陶藝工作室開始做陶生涯,徐永旭的作品歷經〈自由曲線〉、〈戲劇人生〉、〈舞〉、〈位〉、〈神話〉等不同階段,十多年來在時間的流轉與世界觀的變異交融下,從對外在世界到感知、到對內在世界的探求,其作品漸漸逼近存在的核心,醞釀出醇厚的火侯。
不歇止的找尋
徐永旭的作品總是以人形為造型的核心,關懷主軸皆為人,但手法持續轉化。在不同的創作階段中,他折返於抽象與具象的表現手法之間:抽象(〈自由曲線〉系列)-具象(〈戲劇人生〉系列)-抽象(〈舞〉系列)-具象(〈位〉系列)—抽象(〈神話〉系列),不管是抽象或具象,創作者的情感在作品中都傾向於隱而不彰。徐永旭的作品中人物多無頭部,有頭者部者則多戴面具且表情平板,創作者的情感隱匿在作品之中,因為不願明確顯露自身,於是選擇為人物遮掩表情或抽象、接近神話的語彙,因而使作品呈現一種神秘性,這種神秘性在2002年後的作品更為明顯。而從這些形式轉變,也可以看出創作者尋找及探索的歷程。
這樣的尋找,貫穿於他的作品當中。1993年之後的〈自由曲線〉系列作品,致力於形式美感的構築,看似舞動的陶土在三度空間中旋轉、飛舞、懸空,卻不會崩塌瓦解,尋求的是創作者自身對形式平衡的極限挑戰。2000年的〈位〉系列,則以明確的語彙表達對世情的觀察,反諷世人永遠不滿現狀的可笑,儘管已富足擁有卻仍要尋找更多,看似端坐其實卻偷偷踮起足尖的人物,逗趣呈現如坐針氈的憂慮與心焦。2002年的〈神話〉系列中,指向天際的抽象線條、張腿欲奔的獸足、揮張的翅膀,在在都隱喻著在束縛中對自由的尋求,創作者的尋找,到這個階段已然由疏離的外在觀察,深化為內在的生命經驗。
如此由純形式的探索到內在的思索、從外顯的表現更加往內裡探求,事實上是極為貼近「陶作」本質的—-這個需要經過捏製、風乾、素燒、上釉、窯燒……等繁複過程的藝術,在時間的滴答聲中,經過一次一次的修正、火煉,才能臻致完美,這也正是生命的真實樣貌。
凝止卻恆久的時間
徐永旭作品中亦呈現對「時間」的細緻言說。其〈自由曲線〉、〈舞〉系列作品,舞動著的抽象人體,物質本體雖為靜立,視覺上卻猶如舞動,是不停歇的時間之舞,彷彿童話中的紅舞鞋,一直舞到世界的盡頭。這樣對時間的關注,到了2002年的「神話」又再度出現。創作者在數年之後,重拾抽象的人體表現方式,在這系列作品中,固態物質幻化為熔漿一般的閃亮的流體,自天際重重滴落在質感粗獷的台座上,而扭動抽發為單人、半人半獸或男女共體的人形。人形的頭部依然是不存在的,演繹成了向上萌發伸展的芽,嚮往著新生,而相對於此的,流至台座末端的濃重的足滴,恰似一種沉重的羈絆,讓人不能飛逸上天或發足狂奔。在「神話」的一部份作品中,牽繫身與足的流體細絲已然斷裂—-更精確地說,是斷裂的瞬間,而在台座之上的身軀,是停留原地或是順從的發足狂奔的慾望?他猶疑著了。生命中輕與重的抉擇,在這樣的關鍵時刻更顯出其弔詭與艱難。
「如果我們生命的每一秒鐘都有無數次的重復,我們就會像耶穌釘於十字架,被釘死在永恒上。」正如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在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所說的這段話,那立於台座上的難辨人形的體驅,正經歷每一秒鐘的重無數次的重複,而被釘死在那猶豫難決的永恆上。在那永劫回歸的世界裏,無法承受的責任重荷正沈沈壓著那體驅,也壓著觀者。當觀者進入了那斷裂的剎那,也隨著創作者掉進了永恆的裂隙裡。
縱觀台灣陶藝的發展史,早期台灣的陶藝以仿古為主,在1980年代大量接收外來陶藝的觀念,1990年代歐美留學者大量歸國,帶動了樂燒、燻燒、雕塑型陶藝等各種風潮的興起,短短二十餘年的發展過程中,台灣陶藝界呈現百家齊鳴的多樣風貌,徐永旭的陶藝,即在陶塑型陶藝中佔有自己的一方位置。除了從形式內涵解讀徐永旭的陶塑作品,由尺寸來看亦有另一番興味,其作品從最初開始創作,每歷經一個階段尺寸持續增大,一直到2000年〈位〉系列高達322公分達到頂峰,而這個特徵也隱然成為創作者的被辨認的標誌之一,然而在〈位〉之後的〈神話〉,尺寸不再引人注目,我們卻看見關於藝術內涵更細緻的表達,當創作者突破形式的考驗,作品意義將更為深刻,而這也是謬思頒發給不斷自我提昇的創作者的勳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