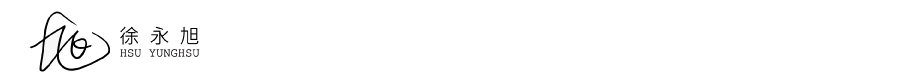徐永旭 身體、踰、泥土
從來沒有停止過的生命、從來沒有停止過的藝術創作,一個國民教育體系下的老師、或是一個運動員、甚至是一個音樂表演者,我們不如說他是一個生命生產者。擔任各種位置的徐永旭,關注到自我與身體之間的關係,無法像笛卡兒的心物二元論,一刀劃開身體與思想,身體的物質性由徐永旭的創作經驗中被打破,重新建立的是什麼樣的一個身體與自我,這是一趟旅程,讓我們一起探索。作品中,徐永旭所聚焦的,是從他的藝術創作生涯所發展出來的方向,複雜而又直接,不再像早期作品中具有一系列不同命題,似乎內容卻沒有命題來的豐富。由創作與生命並行的經驗來看,創作者的不滿足,或多或少說明了人作為自我未完成與匱乏的事實,也成就創作者綿延不斷的創作生產力,與對生命的延續性。
作為一個三十歲才開始接觸陶土的陶藝家來說,之前的生命經驗,無法斷然在創作者離開先前的工作與生活場域後,立刻劃一為二無法完全丟棄,過去如何交融至以後的生命,卻是無限豐富。在接觸泥土之前,徐永旭運動員與音樂表演者的身分,對其身體的訓練所留下的鑿痕,或許是我們可以問的問題。徐永旭從運動員生涯面臨身體極限時,不得不從舞台上退下來,但並不就此就此落幕,也非個人旺盛生命終點,豐富的生命情緒與情感,反倒是沿續生命力的可能。然而生命如何超脫肉身繼續延續,成為徐永旭藝術創作重要起點。我們由徐永旭對自我生命的探索發現,那些林林總總的過去不過像是計畫好的藍圖,徐永旭開始探索消除生命目的性,讓創作與生命完成於自身當中,這種消除目的性的存有方式,生命朝向不確定性而後開展 — 這是一個真正的開展,這樣的創作方式深深的吸引著創作者,這樣的生命故事也牽引著我們的尋究,閱讀著他的創作與生命,保持一個觀看的距離,其實當中是無法將每一個「我」抽離的。這樣創作結果的物件非為其目的而存在,生命不再朝向什麼絕對的終點,而是開放。創作過程猶如生命歷程,它比結果—作品—更令人驚心動魄。循著創作者對創作的摸索,好似探險,對生命的跋涉與翻山越嶺,成為另一種對創作的關注。
當徐永旭開始接觸泥土與創作之後,創作空間、材料、移動成為轉向開始後所面臨的種種矛盾,創作者從既往的穩定開始邁入一個不安定的生活狀態,沒有實質的經濟收入,又面對無法預測的創作未來,在這樣的生命節奏裡,徐永旭企圖對藝術的神秘與不穩定的掌握來詮釋無法掌控的生命。選擇泥土作為材質,可以說是因緣際會,卻無法避免的解讀與生命的質材雷同,有其異曲同工的可塑性、沒有確定狀態的柔軟性。徐永旭似乎想從泥塑中超越什麼,早期的作品大致有一系列的命題,從1993年到2000年,進行題為「舞」、「劇」、「位」的創作,大多以圈泥成型。一開始,還曾以草圖或設計圖構思創作,往後企圖擺脫預先設想好的設計圖的方式。這時的主題都關注在對真實人生的寫照,有意識的反映藝術創作者內心所符應現實社會中的真實感受,探討存在社會樣態的人,帶有強烈的批判性。像是2000年「位」系列的作品中,將人與椅子的形象以坐姿型態融合成一位子的簡單造形,高大筆直的幾何線條,說明忙碌社會下具有多重位置與身份的我們。多重社會枷鎖的發洩之後,創作者開始由外轉尋求由內在湧發出來的情感,作品來到對我與自我的關注,這種轉發的開始是一種隱喻式的空間語彙,我們發現其作品由封閉的圈泥向外打開,此種曖昧不名的晦暗,作品卻像是公共藝術般的陳列於大地或是展場空間,沒有特定線條,但卻是巨大。總讓人以為相似於極限主義作品中的那些空間語彙,所欲給人的壓迫與侵略感,但探究其作品,如地景藝術家那種簡單而又與觀者對話的雕塑風格,蹍轉來到徐永旭的身上,則是由概念出發,讓自身感情延伸,此種概念性的雕塑語彙深深吸引著創作者,這絕非由極限的種角度出發,從簡約作品中所感到的巨大能量的衝擊,所挑戰的絕非只是極限的概念延伸,而是給出了一種生命的力量,等待衝破,簡約造型的藝術形式,更讓我們關注到由材質轉和出這樣的生命力。
2005年的開始,新的體驗不斷的衝擊者創作者,我思故我在,無法滿足徐永旭對生命的渴求與不滿足,生命還能給予他什麼,他還能給出自己什麼,創作主題開始轉向,我在故我思,透過身體如何先為主的來到身體與創作中辯證「我」,這樣的過程像是一段對「我」的辯證,創作絕不是簡單獨立於自身之外的造形藝術而已。泥土材質作為身體的延續、創作作為生命的延續,陶土材質的韌性與外界先入為主的易碎特質,巧妙的與生命特質的接近,在徐永旭的創作中,尺寸大小的觀念不同於極限主義,而是藉由作品的薄和與之相對的大,透過創作中的極度不穩定性,挑戰創作者身體的極限。如同徐永旭所說,毀損成為作品完成的一個部份:沒有毀損,無法逾越。透過藝術創作,通過其他材質,創作者重新解構身體做為物質而存在的唯物說法,將身體層次拉高。一但當創作者進入一個不是以心靈為唯一主宰時,身體對創作材質的靈性,材質與身體交融的過程,這時身體開始具有創新的意義了,如同賦予了一種嶄新的認識論上的開啟。泥土引領創作者重新探索自己的身體,來撫平創作者的不安,創作者沒有一個新的形式或是風格,卻也帶來一種對新的創作方式的開展,丟掉輪廓與框框,指向未滿足焦慮與不安的情緒,無目的的徒手捏陶,感受當下的身體,造形藝術的視覺優先地位似乎留給了觀者,創作者找到一種不先以被觀看的方式開始他的創作,新的經驗再度讓徐永旭延續他豐沛的創作生命力,到此,創作與生命已從平行的兩條線,互相交集、交融。這樣的創作是離開物理時間的當下,是創作者與材質交會的那一刻,如創作者所云,好似戀人般的關係。創作者不但作為作品的生產者,也成就了生命的生產者。反覆的捏塑,凌駕於身體的精神狀態,抱著一種好似走鋼索的心理狀態,不斷的湧發出新的經驗,不斷的經歷新的感受,主體消費自身身體而溢出更多來成就自身,將消費肉身的方式,透過身體延伸至創作材質上,出現一種對自我一種新的體驗,對人的一種新的存在意義,遊戲美學開始,生命也開始。
作者實驗性的再現回憶,創作者又開始處理一個新的議題,回議是否能夠再現,作者每每進入工作是捏陶時,利用攝影機拍下,並自我觀看,努力回憶當初的感受,結果回憶所能達到的非再現又成為一種無法預知的新體驗。作者通過晃動其主體位置,成為流動,或是游動的,讓物理身體與固定時空在其創作行動中重新擺置,錯置,同時也在空間折疊時,折疊出更多秘密的角落,而發現自我的更多皺摺。創作者談到在創作過程中所必須克服的「慣性」,讓作者在克服創作經驗中所產生的慣性,作者以不同的姿勢與泥土接觸,愉悅自己的身體,挑釁出更多湧發的知覺經驗,這種主動嘗試的創作念頭也讓人著迷,這種挑戰焦慮的勇氣也讓人佩服。
徐永旭從先決的形象來決定其創作,預先設計好設計圖,到讓身體直接的去面對陶土,不再迂迴,而不是主觀或是客體化藝術作品的創作方式來從事其創作,而是勇敢的將自己交給泥土,也交給生命。雖說在踏入陶藝之初,創作者企圖挑戰的、否定的是那句老話:「作品進窯後就交給窯的手,等待著開窯的喜悅。」卻也將自己丟給了身體知覺的重新認知。創作的轉折讓我們看見所謂泥土作為創作材質時,其中土與身體之間的互文()關係,模糊且膠著著。如同母親懷胎十個月,母體與子無法分割的曖昧,如同戀人般矛盾與親密。徐永旭主動勇敢的以行動方式來挑戰身體的觸覺,此一主動乃作者創作過程中我們唯一可猜測之意識,這種主動,以一種積極的方式在創作材質的面前放棄自我,赤身裸體的攤現在泥土之前,挑戰身體的疆界,建立新的感官知識,這與後現代所謂去中心的巧妙之處還得令我們再去觀察與發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