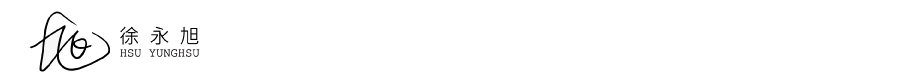徐永旭的巨碑式勞動
徐永旭國際版畫冊
文/陳貺怡
國立台灣美術館館長、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系教授、巴黎第十大學當代藝術史博士
CHEN Kuang-Yi
Ph.D. in Contemporary Art History, Université Paris X- Nanterr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Director of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徐永旭是臺灣著名的陶藝家(ceramist),早年他為了陶堪稱瘋狂的放棄了穩定的教職與醉心的音樂,從1987年成立陶藝工作室至今(2025),創作、駐村、展出不輟,並且累積了一定的國際聲望。不過「陶藝家」這個字眼,顯然無法準確的指稱他以這個奇妙的媒材所從事的所有創作活動。在將近40年的生涯中,他的作品一再蛻變,規模益發宏偉,而他在官田的工作室也逐漸發展成了全臺灣最大的陶窯工作室。
陶藝是世界文明中最古老的技術之一,陶(Ceramics)這個字來自於希臘文keramikos與keramos,同時意味者「陶器」與「陶土」。從做為材料的土轉化為「器皿」,結合了構成生命的四大元素:土、空氣、水、火,並歷經奇妙的物質轉化過程。猶太教與基督教的上帝將自己比喻為「陶匠」,而受造的人則被比喻為「泥土」。根據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古希臘關於繪畫與雕塑起源的傳說,與陶匠 Boutadès de Sicyone為女兒即將出征的情人塑像息息相關。古埃及人的陶俑、艾突斯克人的陶棺,反映了陶在墓葬文化中的重要角色。而臺灣的排灣族則將陶壺視為祖先的創生之處,也是祖靈的家,可見陶在人類文明中堪稱重要的發明,具有神聖的特質且意義非凡。
我想徐永旭對陶的執著,肯定不僅限於技術、美感或功能等其他媒材或可取代的層面。這個古老的媒材,特別是樸質的Terracotta之所以無可取代,且激發了無以數計的藝術家,正因為它能滿足人們在身心靈上的多方需求。而這也就是為什麼徐永旭的作品被認為超越了陶藝,而引起「陶藝還是雕塑」的爭論。其實真正的藝術家無法被學科主義或職業疆界所標籤或定義,例如一向被視為「畫家」的高更(Paul Gauguin),從1886年開始原本為了增加收入而追隨陶藝家Ernest Chaplet學習,但最後卻徹底顛覆了藝術家與陶藝家合作的法則,他不但從塑形到燒製的各階段均不假手他人,並且為其形狀複雜且怪異的作品創造了「陶雕」(sculpture céramique)這個新詞。高更將陶窯之火比喻為「地獄之火」,著迷於樸素的陶土如何透過各種技法與燒製過程而改頭換面!而這種地獄與蛻變的意象顯然完全滿足了他作為象徵主義者的想像,驅策他塑造出一個又一個既迷人又令人驚懼的形象。同樣為陶瘋狂的藝術家還有加泰隆尼亞藝術家米羅(Joan Miró),他稱火為「我們偉大的朋友」,能給我們「帶來他的財富和美麗」。他的最後一件作品是創作於1982年的《女人與鳥》,位於西班牙廣場附近的胡安米羅公園。這座22公尺高的陶雕有若豎立的陽具,中間巨大的黑色裂口則仿若女性的生殖器官,符合超現實主義者關於藝術創造力源於性驅力的主張,而陶則隱喻了宇宙萬物的創生與再生。
反觀徐永旭的創作生涯:始於器形的固守,繼之衍生出有機造形,接著發展出敘事性的人體變形,最終完全放棄了掩蓋物質特性的具象塑造,進入材質的突顯與表現。其中的轉捩點,我認為是徐永旭遭遇到了從陶藝邁向立體塑造的兩個重要挑戰:一是「紀念性」(monumentality,但請容我在本文中譯為「巨碑性」)。此詞不但點出藝術作品最原始的功能與型態(如金字塔、方尖碑或神殿),其與空間或場域的關係,亦指出其源於尺寸、比例和風格之強大或宏偉的特徵。徐永旭從2000年開始,因為戶外展覽與駐村發表的諸多機會,開始面對巨碑性帶來的創作挑戰,因而逐漸放棄光潔無瑕或釉彩繽紛的陶藝技術。他從在美國發表的《神話2004》系列開始燒製裂紋與墟隙;並在參觀完美國後低限藝術家的地景作品後,開始探索作品與場域空間和人體比例的關係,解決支撐與重力問題的同時,更回歸材質本體之純粹性;最後模擬生物繁殖增長的過程,以模組(module)的方式隨場地特性,進行結構增生式的部署,徹底解決尺寸與領域跨越的問題。我要強調的是,這並不是一個從具象到抽象的過程,而是一個如何顛覆陶器的脆弱與精巧,以讓位給陶塑的強大與宏偉之過程,全部體現在所選擇的形式以及技術層面上。
另一個徐永旭面對的挑戰是與「巨碑」息息相關的「勞動」(labor)。從上古至中世紀,藝術作品的生產需要大量的體力勞動,特別是巨碑式的作品,試想一座金字塔的建造需要多少集體勞動力?因此在文藝復興之前並無「藝術家」與「工匠」之別。直至文藝復興將藝術家的腦力與體力分開,並厚此薄彼,始有達文西對雕塑發出的輕蔑之語:「雕塑不是科學,而是一種相當呆板的技術……雕塑家身上的汗水摻雜著塵埃,混和成泥漿。」即便如此,在杜象開啟當代藝術之前,藝術家的創作仍是一種與工作相關的身體勞動,正如Boris Groys所言:「這種勞動的痕跡在作品完成之後仍然清晰可見」,因此宣稱藝術家的勞動不同於工業勞動者的勞動,而是一種非「異化」(alienated)的勞動。很少人在看到那些徐永旭的工作照時不曾為之動容,特別是攝影師們總喜歡強調他的雙手:青筋暴露、粗糙巨大,甚至纏裹著層層繃帶。徐永旭最終回歸「泥條盤築法」,以各種手與身體的使用方式,像羅丹一樣將身體的痕跡結結實實的烙進陶土裡。我們可以將作品視為徐永旭身體的延伸,足以在藝術家不在場時喚起藝術家的身體。這種堅持或許有心理的因素,誠如雕塑家兼評論家Sidney Geist的見解「對材料的愛好是心理的問題,而不是雕塑的問題」,徐永旭也不只一次提到身體對陶土的施力,如何緩解他的焦慮。但我認為更有趣的是,在杜象繼達文西將藝術家從手工的沉重勞動中釋放出來,而當代藝術透過雇傭或觀眾參與,日益強調勞動身體的交換之後,徐永旭卻反其道而行,將藝術家勞動的身體與古老的陶塑技術水乳交融的銘刻在一起,使作品成為「巨碑式勞動」的結果。在虛擬身體(virtual bodies)成為現代人類的生命樣態,而各種科技產品造成感官與認知無法克服的「離身」(disembodiment)時,或許對當代觀眾而言,藝術家徐永旭巨量的身體勞動,不僅是一種崇高美學(sublime)的體現,也總能帶來一些具身的(embodied)撫慰與盼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