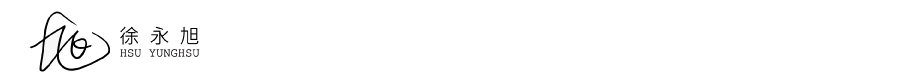徐永旭 泥土裡的時光賦格
2014年09月號No.60 藝外雜誌-藝術家身影
像是什麼不知名生物的巢穴,一個個猶如剖開的卵殼,層疊交錯成一座矗立的岩石。仔細觀看,那些像是細胞般的橢圓造型,就是整個架構的基本單位,它們彼此連接支撐,完成了整體的恆定和沉穩,卻又兀自獨立,宛如是某種存在狀態的切片。或是清澈白皙彷彿是融化的漢白玉,又或是黝黑深沉如流動般的黑色大理石,這些樸實而敦厚的泥土濾去了多餘的雜質,終於搗煉成純淨的瓷土,因為必須保持柔軟的質地,它們在摻入了潮濕的水分之後被細心地包裹,在真正被開啟之前,土質彷彿沉睡一般寧靜地等待著,期待著某個時刻終於被溫暖的雙手接觸,成為藝術家書寫自我的載體,而那些起伏和皺摺就是創作時喃喃自語的聲音和文字,經過了揉捏和塑形,記錄的是那些再也不復返的當下時刻,其中包括了雙手的指紋和力道、每一次的呼吸和心跳,也蘊含了藝術家細密擾動的心思與情緒。
徐永旭的陶瓷雕塑作品,沒有絢麗高超的技巧,只是週而復始地執行相同的動作,但是那看似平淡無奇的舉動卻非無意識重複,而是在固定的形式中去覺察微小的差異與震顫,彷彿生物般蔓生延展,在自有的秩序下擴張成為空間的實存—就像是徐永旭對於自己創作的詮釋一樣:「創作就像是時間序列的切片,而作品就是時間亂序的堆積;在創作中時間流過,我也隨之流進作品,而身體也在慢慢地磨損。」
創作對於藝術家而言無疑是一種情感與精神性的言說,然而表達與完成的方式卻各有不同,可以是激昂地揮灑、也可能是隨興吟唱式的漫遊,然而或許是陶瓷本身媒材上的製作條件與既定程序,抑或是徐永旭天生清晰的方向感或邏輯性,創作之於他更像是一種必須每天執行的日課,必須時時磨練、刻刻砥礪,猶如從不間斷的修業之旅,過程是一步一腳印地明確清晰,而終點永遠在那連綿山脈的盡頭,難以一眼望穿。所以藝術家持續地向前推進,在路途上留下了鐫刻般深刻的步伐足跡。走過了生命中的千山萬水,2009年,徐永旭在台南的官田落腳,建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在這個佔地500坪的廠房內一共有四個窯,包括一座體積20立方公尺的大型窯,「很少有人像我這樣同時擁有這麼多個尺寸這麼大的窯。我幾乎是用『部門』的概念來進行創作。」徐永旭說道。就在我們造訪的時候,他正在執行一個和新加坡建築師配合的建案,需要製作出2800片巨型的陶瓷瓦片,為了因應如此規模龐大且時間緊縮的製作,徐永旭不僅擴增了助手的數量,而每天上午8點半助手開始工作時,他也就展開了既定的每日行程—對徐永旭而言,「產品」和「作品」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概念,助手們幫忙處理和製作的是「產品」以及與創作相關的週邊事務,然而面對「作品」,藝術家則堅持完全不假手他人,因為他認為創作的材料有其必然性,而陶瓷就是必須直接與人接觸,特別是那種身體與泥土相遇時所留下的痕跡,詳實地融入了創作者身體與心靈的狀態,所以,徐永旭必須堅持整件作品的完整而獨立,而基礎就奠定在整個過程中藝術家絕對的參與。「有的時候助手們在午休,我就進到自己的辦公室繼續處理事務;傍晚助理們下班了,我可能還繼續留在工作室創作,甚至一忙就忙到將近午夜才會離開。」妻子和家人都住在高雄,徐永旭為了就近創作,長年在台南藝術大學附近租了一間設備簡樸的小套房,而這就是他每日結束工作後要回的「家」。觀看徐永旭的生活行程,你很容易就發現在他的意識裡,彷彿沒有比創作和工作更重要的事了—這幾乎就是徐永旭現階段生命裡最重要的戰場和舞台,不僅是他最全神貫注的所在,也是他擁有絕對自由的原野、最重視的精神廟堂。
所謂的藝術與人生,對於徐永旭而言從來不是水到渠成般的順遂,因為他性格裡不屈不撓、勇往直前的特質,使得他的人生閱歷回顧起來還帶有些高潮迭起的傳奇色彩,就連徐永旭都笑說自己是「把一輩子當作兩輩子在活」。1955年出生於高雄,徐永旭的原籍是澎湖,父親在年輕的時候舉家遷居至台灣屏東。雖然家境貧寒,好在家裡包括徐永旭在內的三個孩子都天資聰穎,他說自己小時候不怎麼需要太用力唸書,幾乎是「看一看就會了」,也因此比同儕多出更多時間和精力去體驗童年—不僅成績優異,舉凡美術、作文、演講、田徑⋯⋯幾乎樣樣第一,初中畢業之後,按照徐永旭的成績應該可以進入當時的第一志願高雄中學,但考慮到家中經濟的窘境,徐永旭決定把目標放在有公費名額的台中一中體育實驗班,為了加強術科,他幾乎天天一早就苦練田徑,然而卻在距離選拔賽的幾個月前拉傷肌肉,最後只能放棄成為專業運動員的志向;另一方面,因為當時把重心都放在運動上,徐永旭只好犧牲和練習田徑同一時間的晨間英文課,這也使得英語成為徐永旭在學科上永遠的弱點,「一旦錯過了學習的機會,就再也補救不回來,直到現在我的英文就是一竅不通。」徐永旭拿出一本他早年買的英文的陶瓷製作過程的化學書籍,上面密密麻麻寫滿了中文的註釋,「沒辦法,當時台灣這方面的資料太少,我只好自己買書來看,但是英文我完全看不懂,最後就是硬著頭皮閱讀,幾乎每一個單字都查字典。」徐永旭說道,而他這種不認輸又拼命到底的性格,使得他的生命經歷,硬是比別人多出了許多特別的經驗。為了替家裡減輕經濟壓力,1971年16歲的徐永旭進入了屏東師專,剛入學沒多久就被國樂社的招生訊息所吸引,好奇心的驅使之下他決定入社,只是徐永旭沒有像其他大部分的同學選擇吹笛子,而是選了技術難度比較高的古箏。「我的想法是,師專畢業以後要當老師,上課已經要講很多話,所以學樂器就不想再跟嘴巴有關的了;另一個理由是,當時如果古箏學得好,我就可以當家教或到樂器行教課,這樣一來也可以賺錢貼補家用。」既然決定了就一頭栽進去,古箏從此對於徐永旭而言不再是玩票性質的興趣,即便後來畢業開始在小學任教,徐永旭也始終沒有放棄加深他在古箏演奏上的造詣—好長的一段時間裡,他每週三結束半天的工作之後就搭火車北上向古箏名師求教,上完課再趕搭夜車回去,清晨回到高雄之後再繼續回學校教書。
「我一心想成為音樂家,從1982年開始我每年都舉辦古箏獨奏會,除了學校的正職之外,每週還兼教40個小時的古箏課,那個時候我教琴賺的錢是我學校薪水的四倍。」徐永旭這種拼命三郎的生活一直持續到1985年才停止,他決定結束的原因除了長期的勞累已經讓身體不堪負荷之外,還有兩個最重要的關鍵:「當時我已經把家裡的債務還清,認為經濟狀況已經好轉而毋須再賺更多的錢;另外就是深刻感覺古箏不是一項值得我終生研究的課題。」徐永旭說自己在鑽研古
箏樂理和歷史的過程中,發現箏這個樂器有著很大的歷史斷層:「我們現在看到的箏其實是清末民初的形制,而所謂的日本箏其實是保留了隋代箏的形制,而韓國箏則是沿襲了唐代的箏。中國從隋唐之後,關於箏的文獻或資訊其實是一片
空白。」徐永旭說現代人演奏的古箏用的是鋼線,技巧著重在兩隻手的同時彈撥,然而這都是近代才產生的技巧,「古代的箏演奏方式應該更像是古琴,會有彈撥和按壓兩種技巧。然而因為歷史的斷層,使得現今古箏幾乎沒有自己的樂譜,許多曲目都是由近代琴人自己打譜編寫,或是從戲曲中擷取出來的段落。」發現了古箏有其先天的侷限,徐永旭便毅然停止對於古箏的研究,即便當時他已經是台灣古箏界頗有名氣的演奏家了。就在徐永旭停止彈琴之後,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受到朋友之邀一起成立陶藝工作室,當年31歲、興趣原本就廣泛的徐永旭想了想,覺得自己一直喜歡平面繪畫,既然有機會也想嘗試立體的創作,加上和朋友分擔工作室的費用也不算太高,就很隨興地答應了。剛入門的徐永旭從拉胚、上釉、窯燒等基本技術開始自學,但過了一陣子之後,對事情總是追根究柢的徐永旭又開始覺得哪裡不太對勁:「首先,當時陶藝界主要還是在製作『器』,我認為那偏向實用工藝的領域,而我想探索的還是『造型』本身;其次,我覺得在素胚
上淋上釉就送進去窯燒,在無法預料最終成果的狀況下,好像有點不負責—藝術家應該要完全地掌握最後的成果,如果不符合預期,那就算是失敗;再者,我認為造型本身還是要具備動態和美感,那是一種創造,而不是按圖施工。」徐
永旭坦言,因為自己對於陶藝的理念和當時主流的陶藝家們不太一致,所以從1986年到1992年他決定不假外力而自己進行關於技術和藝術理念上的創造工程,也就是這個時候,他蒐集了許多國外的英文陶藝書籍,然後一字一句地查字典研
究。歷經了長達六年的摸索,徐永旭覺得自己準備好了,也開始在陶藝界嶄露頭角—1992年,他開始參加陶藝比賽,1994年獲得了台北市美展的陶藝首獎,自此之後徐永旭算是在台灣的陶藝界闖出了名堂,在各種比賽獲獎不斷;1996年
他開始在商業畫廊展出陶藝作品,希望獲得收藏界和藝術市場的迴響。
「我很清楚自己是一個需要舞台的人,從少年時代練田徑、後來彈古箏、一直到做陶藝都是如此,我希望展現自己的能力讓別人看見。」徐永旭非常直接了當地自我分析。從1976年就開始在小學任教的徐永旭,1998年決定放棄還有兩年就可以領到的退休金,毅然辭去教職專心創作:「因為我覺得隨著年齡的增長,體力和時間都越來越有限,我希望可以更全心在創作上。」徐永旭說,長期以來最照顧自己的人,就是同樣也從事陶藝創作的太太林秀娘:「我辭去教職時,她雖然焦慮卻也完全支持。直到現在雖然平常分隔兩地,但她只要一有空便會從高雄到台南來。」徐永旭笑說:「她知道平常我對吃的不太在意,每次來總是準備一大堆水果,結果打開冰箱,發現上次帶來的我常因為忘記吃而放到壞掉,她總是默默地幫我清理掉然後換上新鮮的。」而這份溫柔而龐大的支持,也使得徐永旭在創作之路上走得更加堅定。2000年,徐永旭首次出國赴韓國參加工作營,展開了他自己所謂的「離家出走」的旅程,而這段流浪的經歷也成為其創作表現的分水嶺:「2000年以前我的作品風格比較具象和說明性,離開台灣和熟悉的環境之後,獨自在外生活的經驗讓我更清楚地面對自己,有了更多內觀與內省。」2003年,徐永旭重回校園,進入台南藝術學院(現為南藝大),他更進一步地思索關於堅持用陶瓷這個媒材的核心概念:「陶瓷因為需要窯燒,為了怕空氣在加熱之後膨脹導致破裂,所以陶瓷作品需要開口和中空。當時我就想,既然這個媒材本身的技術問題是必然的,那何不乾脆把造型打開來,讓它變成開放的碎片狀?」而這個想法也成為他後來以類似貝殼或花生殼狀的小土塊為作品造型的基本單位的濫觴,這些看似雷同卻又從不重複的造型,也呼應了徐永旭認為生命就是一個接著一個的循環,在低限的重複累積中成為巨大而充滿張力的造型。
「我不卑不亢地用陶做創作。」徐永旭說:「因為陶瓷所具備的實用功能對創作而言是一種包袱,所以更有挑戰。雖然一開始接觸陶是誤打誤撞,但現在我卻是有意識地選用這個材料。」徐永旭回憶,自己2005年時在美國紐約第一次看見包括Michael Heizer、Fred Sandback、Richard Serra等藝術家大型的空間雕塑作品,當下就覺得深受震撼:「那對於觀眾來說是一種很直接的、身體與空間的互動關係,和我在創作中探索的議題是一致的。當時我就問自己:『如果已經有藝術家已經把作品發揮到這個程度了,那我還能夠再向前推進些什麼?』」「材質,」徐永旭說道:「如果別人用的是鋼鐵或其他媒材,那麼我的特殊性就在於我選擇了陶瓷。促使我繼續創作和思考的,就是持續探討材料、空間和人三者的結合。」「身為一個創作者,我總是希望自己的每一個階段都能比前一個階段更精彩一些。」在偌大的工作室空間中,徐永旭穿梭在陶窯和作品之間,身形雖然和周遭的龐大物件不成比例,然而你卻並不覺得藝術家是渺小的,相反地,從他身上所迸發出的堅定的能量,彷彿使得整個的場景都是他的王國、他的戰場及其終極的信仰所在。
「只要想到能夠繼續創作,而且作品又能夠有新的跨度,我就覺得好興奮。」徐永旭用篤定而熱切的目光,看著我如是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