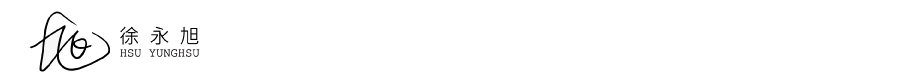永遠向陽:徐永旭的生之慾
「一個畫家如果不被他自己的畫所轉變,為什麼他要畫?」這是傅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晚年提倡的自我塑造、自我轉變、自我突破與自我創新,堅決不止於一般所尋求的自我與自我認同(self-identity)。與其努力回歸主體,傅柯關注的是主體化的過程,藉由極限體驗和越界行為,不斷重複一件事情,累積直至對自己產生影響,繼而突破既有的自我。1徐永旭可謂台灣雕塑藝術家中實踐傅柯哲學最鮮活的例子,他在1986年成為臺灣雕塑藝術的天降奇兵,縱觀他從自習陶塑起家直至今日獲頒吳三連獎藝術獎,一路走來崎嶇蜿蜒卻無畏艱難迎向各種挑戰。這樣的態度亦見於他作品淳厚的氣質、宏大的尺度與盤曲的生成方式,其過程是一場極端痛苦的肉身硬仗,但憑藉著突破知識範疇並超越自我的恆心毅力,他激發不經此途徑無法企及、過去不知曉的原創性,最終蛻變出述說自我生命的鉅作。
追溯徐永旭六十八年來不同人生階段的事蹟,絕境、契機與衝決相互交織,我們看到他是如何形塑了他的自我觀、人我觀、世界觀。無論是面對生命抑或創作,他此生必然會是一部不畏挫敗與煎熬,頑強奔前的奮鬥史。
為聯考捱餓的孩子
1955年,徐永旭誕生於高雄一個並不寬裕的家庭,他是家中排行第十二的老么。他自小考試名列前茅,獲得運動和美術競賽的獎盃如囊中取物,畢業時順理成章保送高雄二中。
基於傑出的運動細胞,徐永旭一進初中即被相中延攬入田徑隊。不過在教練對體訓的嚴格要求下,漸漸地他課業荒廢到險些留級,尤其英文在第一次月考之後再也不曾及格過。在升學壓力輾壓而來之際,他將未來希望寄予全國賽保送高中。「我在初二時曾拿下全國百米第三名,我覺得我有機會」,十三歲的徐永旭對自己的實力相當有把握。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在三年級下學期的選拔賽中,徐永旭才剛起跑就「啪!」的一聲拉斷了足筋,兩年以來所有的血汗前功盡棄。他無可奈何重拾課本準備聯考,但第一次的模擬考,國英數社自滿分520分,他卻考不到110分。距離七月的聯考僅餘三個月,面對這項不可能的任務,幸而他在書店翻書時發現了一塊浮木——收錄了密密麻麻考題的考古題庫,「這時候念課本一定來不及了,我應該把時間全部拿來死背硬記考古題庫上面的考題。」家裡負擔不起一本七元的考古題庫,科目這麼多,怎麼辦?他靈機一動和媽媽商量:「妳給我上學帶的便當蒸過之後味道不好,吃了會想吐。不如妳每天給我二塊錢,我去福利社買東西吃。」自拿到午餐錢的第一天起,中午全班低頭開動之時,徐永旭獨自跑去外面灌水充飢,等大家用餐完畢他再回教室。四天下來湊足錢買一本考古題庫,他再利用四天的時間寫完整本題庫,如此以四天為一單位勤練考題,不久已滾瓜爛熟到瞧一眼題目便知道答案。
英文老師也意外成為他的貴人。英文老師常常出隨堂測驗,考90分以下少一分打一下,徐永旭總是在20到30分之間擺盪,據他形容:「一雙手被打到像紅龜糕一樣」。幾天後被打得受不了了,他索性找老師談判:「都這個時候了,我把所有的時間拿來念英文也多不了幾分,打死我都對我沒幫助,你能不能讓我用這時間去念別科?」老師思忖一下道:「行,以後上英文課你就自動消失吧。」從此英文課不見徐永旭的身影,他翹課去學校隔壁的棒球場念書了。
一轉眼月曆翻到七月,莘莘學子無不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踏入考場。待放榜公布考生名次,師長看到「徐永旭」這名字時驚詫不已,這孩子竟然衝出全校前十名的成績!徐永旭的英文仍牢不可破地釘在20分,但是社會和自然幾乎滿分,數學逼近90分,高雄中學的錄取標準是317分,徐永旭拿下356分,意味著即使英文抱鴨蛋回家,他依然能昂首踏入高雄中學的校門。不久前大家還認為他考上高中會是「太陽打西邊出來」,徐永旭很感謝當時英文老師網開一面,不過對於一個還在成長發育卻經常飢腸轆轆的孩子,最高興的莫過於總算可以好好吃午飯了。
生之慾
經過苦讀拼上高中,讓徐永旭對讀書產生了興趣,遺憾的是家裡經濟捉襟見肘,到高一下學期已不再能夠負擔他的學費,他迫不得已轉到有政府補助學費的屏東師專(現屏東教育大學)。正是在這裡,開啟了他與音樂和藝術的淵源。
如同許多藝術家一樣,徐永旭從小即為美術比賽的常勝軍,不過他文武雙全,並未獨鍾哪一項才能。真正熱衷於藝術,是在遇到《生之慾》講述天才藝術家梵谷的傳記小說。梵谷貧困、孤獨、病痛纏身,一輩子僅賣出過一幅畫,卻有堅強的意志去追求美:「即使我不斷地遭受挫折,也不灰心;即使我身心疲憊,哪怕是處於崩潰的邊緣,也要正視人生」。小說附有梵谷畫作的圖片,農人飽經風霜的臉龐和群鴉振翅下的麥田都讓徐永旭著迷不已。2夜晚裡宿舍同學們墜入夢鄉,唯獨他躲在被子裡徹夜不眠,執著手電筒讀完梵谷傳奇卻悲慘的跌宕人生。闔上書本之後,「一種生命從黑暗中迸發出來的感覺」在心底迴盪不已,他扛起畫板、畫架、畫紙和小畫箱,走到戶外四處寫生。執著成性的他越畫越狂,到了寒暑假也不回老家,獨自在外從早畫晚,往往一天畫出十多張畫才善罷甘休。為了賺錢購買畫具和顏料,他在學校打掃餐廳和廁所,每月領到工資就搭車去高雄採買。在那大街小巷飄揚著民歌的年代,少年徐永旭壓根不知道民歌是何物,只要能畫畫便感滿足。
破碎的大學夢
在屏東師專第五年,徐永旭抽到免服兵役的籤,這對許多人來說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卻不幸擊碎了他的讀書夢。
徐永旭一直對唸書充滿憧憬,他盤算著考進高雄師範學院(現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系,之後進研究所繼續深造,同一時間報考高普考,藉以保證未來在教育行政上的出路。無奈依然人算不如天算,連續三年教育行政沒有出缺,他連報名高普考的機會都落空。而三年來考插大,他次次考得第二名,卻因為其他服過兵役的同儕能靠加分擠進大學窄門,名額一滿也沒他的份了。二條路皆堵上,讀書夢碎了一地,徐永旭只有認份地留在小學裡教書。
彈古箏的那段過往
國樂是屏東師專的特色教學,徐永旭一進學校就聽到學長彈奏古箏泉水叮咚般的的悅耳之音,因此在選修樂器時挑了古箏,並在這方面展露長才。
在高普考和插大考鎩羽而歸之後,恰巧《奪標》和《五燈獎》等電視節目在全國掀起一股炫風,吸引不少人對古箏躍躍欲試,徐永旭遂在教書之餘將時間投注在教古箏上,以此賺取外快和支援家計。市場競爭頗為激烈,有的學生來看一眼徐永旭的教室隨即離去,或者學了一個月就不來了,好強如徐永旭嚥不下這口氣:「我一定要教到我來挑學生,不會讓學生挑我!」
1978年,徐永旭開始每個月隔週的星期三,趁下午教師進修時間不用上課,北上找古箏專家黃得瑞拜師學藝。早上第四節課的下課鐘聲一響,他直奔火車站搭一點鐘的對號快車晚上九點到臺北,在老師家上課至十一點,再搭公路局夜快車返抵高雄,趕在七點四十分到校上第一節課。幾年後高速公路全線竣工,「我改坐國光號去臺北,車程只要四小時二十分鐘,傍晚六點一定到得了,不但不會塞車,中途還附贈一杯柳橙汁」,徐永旭回憶那段舟車勞頓卻充實無比的時光,臉上笑容格外燦爛。他把握這多出來的寶貴時間,又找了二位老師(沈柏序、陳國興)精進琴藝,每次來臺北要上課至半夜才罷手。六、七年之後,徐永旭從素人老師進階為售票演出的專業樂手,在臺北實踐堂、高雄至德堂和至善廳以及屏東共辦了五場個人獨奏。
一頭栽進陶的世界
徐永旭沒日沒夜地投入古箏學習、教學和表演,還得在學校教書,到1985年終究把身體搞壞了。他一位極為要好的古箏老師無預警地腦溢血猝逝讓他深受打擊,加上他越懂古箏越發認知到它的侷限,他將古箏收起來,就此封琴告別陪伴多年的樂器。
半年悠悠而過,徐永旭將精力放回繪畫上,學校裡一位同事見他懂藝術,邀請他一起開設陶藝工作室。1986年,31歲的徐永旭和同事各出資十萬元,先從陶土買賣的小生意起步。他們說服太太共同參與,放學後四人在工作室裡製作泥土。先生負責練土和切泥土,太太負責用塑膠袋分裝,隔天再叫貨車送到開設陶藝班的幼稚園和小學。遇到空檔時間,同事會做陶藝品販售或者教授學生收取學費,徐永旭則負責充當助手。他在一旁觀看同事做陶時總想試試身手,但求人不如求己,他於是蒐羅凡是含有關鍵詞「陶」、「瓷」的書,一本也不放過,從此以後一頭栽進陶的世界至今難以自拔。
四年之後,徐永旭已經在自家屋簷下蓋起一座柴窯,拉起不小的胚創作大器物。適逢台灣雕塑藝術開枝散葉,1990年他找上臺灣現代陶藝推手的楊文霓,想穩紮穩打從初級陶藝學起。不料楊文霓的創作方式相對嚴謹,她習慣先做實驗,再做小的模型,接著進階到大一點的模型,唯有胸有成足才會放手製作作品。在她眼裡,徐永旭三兩下「蹦」出來的作品頂多稱為「大試片」。她也認為所謂的陶瓷藝術品應該是要放在手裡把玩的,徐永旭的作品卻要往後退好幾步才窺得全貌。雖然創作方式迥異,但在一年的時間,嚴謹創作的態度對徐永旭往後的藝術之路影響頗深。
離開楊文霓的工作室之後,徐永旭索性又買書在家研讀。他請託朋友從美國帶回一批外文書,以高中聯考英文20分的程度,靠著牛津字典、萊思康電子字典、化學辭典三個翻譯神器奮發圖強,連介系詞無一放過逐字查找,將詞彙排列組合成足以理解的中文句子。他甚至將電子字典的按鍵按得一片模糊,看不清字母的標示。終於耗時二、三年的時間把那些材料、科技相關的書籍看完,像海綿一般吸收各種新知直至充沛飽滿。
每個藝術家在累積一定的作品數量之後,無不期待辦展覽發表和銷售作品,徐永旭也不例外。可是既無人脈亦無知名度,一介素人如何取得辦展的機會呢?徐永旭針對活躍於檯面上的前輩,展開一番透徹分析,「我發現真正被視為陶藝家的創作者有三類:一、藝專和大學科班出身的藝術家,二、國外留學回來的陶藝家,還有三、從名家工作室像是天母陶社出來的陶藝家。」相較之下徐永旭顯然屬於異類,那麼還有其他門路嗎?「有,就是參加比賽,這類藝術家大約拿到二到三次獎之後,就會有人上門邀請辦展覽。」
1992年,徐永旭初試啼聲參加省展便獲得入選,他頓時信心百倍,「工作室才成立六年,我悶著頭能做出這樣的水準,我覺得我有機會!」到了1994年,徐永旭在台北市美展一飛沖天拿下第一名,此後任何比賽都會打入前三名,「而且沒有得到第一名就很不開心」。1996年,果真有畫廊上門請他辦展覽了。
個人風格浮現
徐永旭在1992年發展出獨特的個人風格,他的創作歷程亦是以此時間點為開端。徐永旭從「舞」的母題衍生出「戲劇人生」的子題,帶有動物意象的單一造型如《鵠》可看出他簡化具體對象物的傾向。而具有舞蹈和音律感的作品如「共舞的日子」、「舞台上的人生」等系列不再是有口的容器造型,結構呈現複雜化並出現虛實的空間概念,這些作品頗像亨利.馬蒂斯(Henry Matisse,1869-1954)三聯壁畫《舞蹈》(The Dance,1910年作,)的立體版,惟徐永旭將舞者交纏成一體,人與人糾纏不清抑或唇齒相依的關係,散發出強烈的隱喻暗示。
在藝術賽道上提足起跑
1998年,徐永旭43歲,這是他成為專職藝術家的關鍵一年。他只要再撐三年即可自小學退休,但他的願望是心無旁騖地投入創作,於是在太太的支持下,他牙咬一咬離開了任職22年的教職。2000年,他在朱銘美術館舉辦首次的戶外展覽,以七件戲劇感十足的大型雕塑將戶外轉化成劇場,《如皇》、《似妃》等作品猶如埃及法老與妃子傲視天下,同時人形與座椅合為一體,展現邀人入座的氣度,讓藝術界對徐永旭刮目相看。
然而驟然的職涯轉變,徐永旭很快認知到靠展覽維持家庭收入是不切實際的期待,「曾經一卡車的作品運去展覽,結束時只收8000元回來」。2000年的中國以超音速奔往現代化和經濟繁榮,徐永旭為另謀出路隻身到上海闖蕩,卻在落地之後體會到這裡的創作和生活環境和臺灣尚有一段距離,在異鄉單打獨鬥時吃足了苦頭。
單就創作而言,在臺灣買陶土一通電話便能一切包辦,但是在當時的上海他必須親跑一趟二百多公里以外的宜興,向陶土廠買下一座「散裝」的土山,自己得想方設法將土山運到另一個工廠練土和包裝,再運回上海的工作室,這中間不論是叫貨車、運輸、找人搬運、取貨等,每個環節均須耗費心力與金錢交涉,到最後拿到陶土的時候成本早已遠超過預算。一個人居住遠方,內心的孤獨也難以消解。在小小的出租房裡,寒冷刺骨的冬夜裡睡不著覺,身體蓋不到被子的地方凍得發疼,他整晚縮在二層的被窩裡望著映射在牆壁上的窗影發呆,窗影中凝露彷彿流動的水墨緩緩流下,一種有家歸不得的淒涼感油然而生。
這二年磨得徐永旭身心俱疲,他打消了在外深耕的念頭,又憶起那不曾實現過的讀書夢。2003年,徐永旭靠同等學歷考進臺南藝術大學,以48歲之齡成為該校美術碩士學程開辦迄今年紀最長的研究生。
與死神擦肩而過
在臺南藝術大學四年期間,徐永旭念起書來比任何人都像學生,甚至有三個學期到美國駐校創作和展覽交流。學校規定畢業門檻是修50個學分,徐永旭卻修了67個學分,幾乎等同於多拿一個學位了。
2004年至2005年,徐永旭的創作再往非具象邁近一步,發展出造型簡單,看似碎片或局部的樣態,有的像是枯葉,有的讓人聯想到路西歐.封塔納(Lucio Fontana,1899-1968)的畫作,主體上出現驚心動魄的割口,亦開始以不帶敘事指涉的創作年份為作品命名。不過沒有多久,這個階段就過渡為另一個劇烈的轉變。
2005年春,臺灣南部被久久不消散的雲雨籠罩,接連多天下著滂沱大雨,徐永旭在一停車場地下室已形成小型瀑布的階梯上失足一路滑到下層,另一回在家滑倒在泛潮的地板上,二起意外似乎預示不詳的事故即將臨頭。一日他驅車前往學校,在高速公路上行經積水的彎道時,他的車子居然浮了起來,車子忽內又忽外飄移,待其中一個輪胎觸碰到地面,車子霎那間畫起圓圈不住旋轉,直到撞上正向路邊的護欄才停下來。此刻許多車輛從一旁呼嘯而過,徐永旭幸而躲過一劫。
有時在經歷過死亡近在咫尺的衝擊,反而能激發出一人內在深處最真實而純粹的力量,催生出人生之中斷裂式的轉折,這場生死一瞬的車禍即是對徐永旭創作走向影響最大的奇異點。
徐永旭的原創語彙
徐永旭與死神擦肩而過,有一段時間面對創作時腦袋一片空白,只能下意識的將一球球陶土捏成凹形,如此重複了好幾天。漸漸地他一邊做一邊觀察自己的狀態和變化,如何將陶土延展到最大最薄而不倒塌?倒了再重來,等到獲得第一個沒有倒的成果,他研究是什麼因素使它安然無恙,下回他將那項因素抽除,讓自己恆久維持在一個戰戰兢兢走鋼索的狀態。做到後來用手捏出來的東西不倒了,他換用拳頭來搗,用手肘來壓,每一步拒絕慣性的出現,每一天著了魔似地尋找自己的「界」。「我像是站在一個磚塊堆砌而成的塔上,不斷地抽出腳下的磚塊,將自己維持在搖搖欲墜的狀態,最後我會站在甚麼樣的東西上面?」直到後來他意識到一切努力均是慣性使然,這才回歸最原初的狀態,而在此時終於感受到他一心一意企圖逾越的「界」。
徐永旭自發地以實踐和鍛煉去建構自我的價值觀,恰恰與他在校所接觸到的傅柯思想不謀而合。傅柯的思想偏向個人化的哲學生活,視哲學為一種修身時實踐的技藝,將哲學體現在生活當中,謂之「生存美學」。在他的觀念中,人應該有意的、自願的和反思的去行動,尋求自我轉變,改變自己的存在方式,繼而建構出自我。經過極限體驗,從而跨越一些約定俗成的範疇或借鑒,這是思想原創性所不可或缺的,這樣的主張讓徐永旭大有共鳴如遇知音。3
從2006年開始,徐永旭以此法逐漸推展出今日我們所熟知的藝術語彙。他的藝術是透過身體去接觸泥土,在有限的時間和當下的空間裡,肢體和材料的關係不斷交互影響,所有形成的肌理紀錄著順勢而為的過程,同時反映溫度、濕度、重力等環境條件的細微變化。他不做設計圖也不事先規劃,有了創作的念頭便著手執行,作品量體和土色是唯一的預設。
他選擇人類文明發展以來最原始的媒材,採用最簡單的創作手法。「人類最早在新石器時代,甚至更早之前就使用泥土製器,製作方法是一坨泥土放在手裡使之變薄,變成凹形承裝物質;再進步一點則發展出條狀,盤繞成形。」徐永旭經由搓、壓、捏、按將土製成杯形、條狀或帶狀,亦可說是鳥巢、枝條、海藻等天然造型,重複堆疊、盤繞而成厚度最薄又尺度最大的陶塑。創作中的徐永旭不斷試探體力的極限,用非凡的意志力拚搏,將自身置於困頓之中,再由其中開顯出「我」。至此他已「去除過去習得的知識,回歸生物的原始狀態,像是蜜蜂築巢或蜘蛛織網一般,本能地面對創作」。他在天地人所構成的世界中展現生命現象與生命意義,聽憑自然生長出來的形體宛若貝類集合體、蟻塚、海底礁岩,也有千絲萬縷的捕夢網,光與影在繁複的罅隙、曲線、溝痕之間流動,而身體勞動所遺留下來的蛛絲馬跡,將藝術家再真實不過的存在狀態和轉瞬即逝的情感定格。
徐永旭後續的故事已經眾所週知了。他在藝術的道路上結實累累,2008年參加日本美濃國際陶藝競賽,從五十多個國家、三千兩百多件參賽作品中,以長269公分、寬118公分、高222公分的大型雕塑《界.逾越》脫穎而出,成為該獎項十六年來首次的外國首獎得主,更是臺灣摘冠的第一人。同年他開始打造今日已達五百坪規模,世界名列前茅的燒窯個人工作室。2019年,高雄市立美術館為他舉辦「以光織界:徐永旭的藝術世界」個展,呈現他自2011年至今最重要的二十一件代表作,其中《2019-1》一體成形近2層樓高,是他挑戰體力、技術與窯燒條件極致的巨型創作。2021年,他獲頒有臺灣諾貝爾獎之稱的吳三連獎藝術獎及第一屆台灣陶藝卓越獎,2022年在香港巴塞爾藝術展博下國際重磅媒體《紐約時報》的版面。在展覽方面,他已經累積四十五次的個展。
「他想玩〔土〕就讓他去玩一玩,怎麼知道後來變成這樣?」回顧徐永旭的創作緣起與發展,不僅他自己始料未及,連他太太都覺得不可思議。生活和工作中的主要興趣是成為你當初所不是的另一個人。假若你開始撰寫一本書時,你就知道最後你將會說甚麼,你認為你會有勇氣去寫這一本書嗎?……這種遊戲之所以值得,乃由於我們不知道結局是甚麼,傅科曾如此評道。4生命於徐永旭同樣不是規劃的,它是自由的、創造的,他不喜歡自己的生命歷程是重複的,甚至是可以預示到將來。5從過去以至未來,徐永旭始終時時刻刻書寫人生嶄新的一頁,即使行經幽谷仍從黑暗中迸發出熾盛的「生之慾」,永遠向陽。
參考資料
- 黃瑞祺,〈自我修養與自我創新:傅柯晚期的主體/自我觀〉,《傅柯三論:傅柯晚期思想研究》,台北:唐山出版社,2018.04.01,頁59
- 歐文・史東(Irving Stone),《生之慾》(Lust for Life),余光中譯,台北:九歌出版社,2009.12.01
- 黃瑞祺,〈自我修養與自我創新:傅柯晚期的主體/自我觀〉,《傅柯三論:傅柯晚期思想研究》,台北:唐山出版社,2018.04.01,頁46-48
- 黃瑞祺,〈自我修養與自我創新:傅柯晚期的主體/自我觀〉,《傅柯三論:傅柯晚期思想研究》,台北:唐山出版社,2018.04.01,頁44
- 徐永旭,〈界.踰越〉,2006
http://yunghsu.net/essays/2006-%e8%97%9d%e8%a1%93%e8%a7%80%e9%bb%9e-%e7%95%8c%ef%bc%8e%e8%b8%b0%e8%b6%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