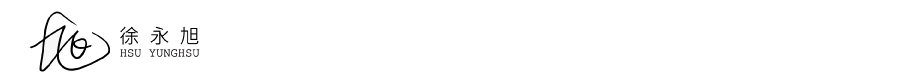肉身苦行
1.
徐永旭是一位讓人一眼看到作品便會感動的藝術家。這不僅是因為他的作品的造形本身具備獨特的美學意涵,更是因為他的作品紀錄著他為了探索並突破自己生命力與創造力的極限所經歷的每一次艱苦的試煉。我們甚至可以說,他的每一件作品都是嘔心瀝血的的造形。
徐永旭在一九五五年出生於臺灣高雄,一九七五年從屏東師專畢業之後,長期從事藝術創作,直到二○○六年又從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獲得碩士學位。如果從活動經歷來看,他是從一九九○年代才開始積極參與展覽,但是就藝術創作的探索歷程而言,他應該更早以前就已經開始。換句話說,當他在一九九○年代積極投入展覽活動的時期,事實上他已經處在思想相當成熟的狀態,也因此,在九○年代那個臺灣的當代藝術蓬勃發展而充滿誘惑與陷阱的年代,他依然可以堅定地以黏土這個歷史久遠的媒材去表現自己藝術創作的當代思維。
此外,徐永旭也是少見的一個思想深刻而頭腦清楚的藝術家。雖然在創作中他讓身體專心工作,但是他卻具有一種能夠將身體所經歷的一切活動與情緒狀態一一陳述出來的思想能力。這樣的能力,一方面意味著雖然創作中他沒讓思想指導身體,卻又能夠敏銳地讓身體的活動轉譯成為思想的活動,發展出他關於身體的思想觀點,另一方面也意味著他的思想都是來自他對自己創作活動的反省,而不是別人的思想在引導他創作,即使在學習的過程中,他必須研究各種當代藝術的理論,但這些理論也都必須經過他實際的肉身苦行,才能轉化成為他自己思想的參考材料。也因此,即使二○○三年重回學院進修這段期間,他確實也曾得到更多理論的洗禮,但是他都能讓這些理論幫助他更深入去理解自己,去反省自己,而不是讓自己迷失在理論的陷阱之中。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徐永旭,除了生命思想已然成熟,在創作上也已經進入一個不需要理論去穿鑿附會而能自己充分發揮的階段。這個事實,我們可以從二○○八年他在高雄市立美術館的「黏土劇場:徐永旭個展」得到證明。這個展覽的作品,都是他近幾年以黏土為材料經過窯燒完成的「極大極薄」的造形作品;依照他自己的解釋,這些都是他為了逾越自己身體的極限而創作出來的作品。他所要逾越的不僅僅是身體的體積界限,也不僅僅是身體的活動範圍,而是試圖逾越他對自己身體的感覺與認識。做為一個藝術家,更重要的是,他試圖讓身體隨著造形的伸展,脫離慣性,發展出不受慣性制約的藝術原創性。
2.
雖然我們一再地說徐永旭的作品是在探索身體的極限,但事實上,我們會發現,在他近年的作品中,我們看不見任何狹義的身體,例如身體的圖像、象徵或符號,包括藝術家自己身體的具象表現,我們看到的是一個一個經過堆疊捏塑與窯燒而成的黏土造形。
在創作這些作品的過程中,徐永旭選擇不使用任何工具,而只是以自己的手掌與指頭一圈一圈銜接堆疊土條,再以不斷反覆的搓揉,擠壓與捏塑的動作,讓薄度處在臨界點的造形加高發展,讓造形接受往上加高的重量考驗,從而決定造形的偶發構造。這些動作彷彿春蠶吐絲,從自己身體吐出綿延不絕的細絲,纏繞出一個原本並不存在的造形。春蠶具有一種本能的目的性,目的在於纏繞出一個橢圓體將自己包裹其中,而徐永旭的創作卻不是無意識的本能,而是刻意讓本能在目的性不明確的狀態中釋放出來。兩者雖然不同,但這個聯想,一方面還是可以用來形容徐永旭的創作活動是一種肉身苦行,另一方面也可以讓我們發現藝術作品的媒材與藝術家的身體之間存在著一種類似血緣的關係。
在徐永旭的創作中,他的身體已經隨著媒材進入作品之中。他的整個身體透過雙手,跟隨著土條在大型工作桌上的伸展與堆積而移動,在這一再反覆的身體移動與手指捏塑的過程中,身體已經化身到黏土之中。這時,材料也已經承載著藝術家的身體,進入一個藝術家自己也尚不知曉的苦旅。誠如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在《眼睛與精神》(L’oeil et l’esprit)一書也曾經提到:「事實上,我們不會看到一個精神能夠繪畫。畫家其實是把自己的身體放進世界,才能把世界轉變為繪畫。為了理解這種身體移轉,我們應該要重新找回正在活動中的真實身體,這種身體並不是一塊空間的碎片,也不是一堆功能的組合,而是視覺與運動的一種交織狀態。」相同的,徐永旭也是把他自己的身體放進黏土之中,才能將黏土轉變為造形;而創作中,他的雙手與他的身體運動也處在一種交織狀態,這個交織狀態讓他雖然進入一個自己尚不知曉的旅程,卻能感受到身體正在隨著雙手與黏土的接觸與相互滲透,而發展出超乎自己經驗的生命情境。這個情境,有痛楚,也有驚喜。那是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旅程。
3.
這個不確定的旅程,雖然乍看充滿冒險,但是對於一個具備充沛造形爆發力的身體而言,它也是藝術原創性的泉源。
在當代藝術中,許多偉大的經典便是來自不確定性,而這些作品之所以令人感動,在於創作過程的不確定性讓人看到藝術家朝向未知走去的身影。即使波洛克(Jackson Pollock)是在範圍明確的畫布上創作,但是他的行動繪畫的滴畫法便充滿不確定性,讓身體取代視覺邏輯,進入他身體活動同時才發生的世界中。當代著名的女性藝術家賀絲(Eva Hesse)曾經使用玻璃纖維,讓這個從氣態進入固態充滿變數的媒材,隨機展現出不規則造形,並轉變了她創作地點的空間狀態;她的作品感人,就在於它們紀錄了她透過媒材展現出來的創作過程與生命姿態。
藝術理論家柯勞絲(Rosalind Krauss)在《現代雕塑的演變》(Passages in Modern Sculpture)一書中,便曾稱呼這種藝術為「過程藝術」(process art)。她指出,過程藝術關心的是形狀的轉變過程,它們透過溶解去重新提煉,透過堆疊去重新建造;在重新構築的過程中,它們所完成的藝術物件或造形,被賦予了一種人類學意象;當一個藝術家將注意力集中於材料的轉變過程,他也就進入了他自己所創造的一個彷彿原始狀態的雕塑空間中。
在徐永旭的作品中,我們也看到過程藝術的精神,藝術家在形狀的轉變過程中,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審美經驗。這個審美經驗,不再遵守既有的視覺邏輯,反而朝著一個挑戰既有視覺邏輯的方向,使我們在沒有規則可循的狀態下,重新提出一個可以將注意力集中在創作過程的審美態度;也就是說,面對徐永旭的作品,如果只是停留在形狀,我們只會是眼睛在看,但如果能夠從形狀進入情境,我們的身體也會跟著作品進入一個尚未定義的世界之中。也就是說,藝術家給了我們一個正在他作品中發生的空間與時間。
或許我們都已經處身在一個被給予的空間之中,但我們不見得參與它的創造,而徐永旭的作品,雖將自己豎立在這個已經存在的空間中,卻又重新定義了這個空間,並且發展出一個可以讓人覺得遺世獨立的空間。這些黏土造形,把我們帶進了一個可以讓我們自己的身體重新去定義的空間。
或許我們也早已在一個被決定的時間之中隨波逐流,但是一旦我們來到徐永旭作品的情境中,便會發現另一個時間定義。藝術家以他的手掌與指頭捏塑土條的每一個反覆動作,既儲存了手指的情感狀態,也儲存了這個情感狀態的時間過程。他的造形,儲存了痛楚與驚喜交織而成的身體時間。這是藝術家以他自己的身體定義出來的時間,它也把我們帶進一個完全不同於現實生活的時間經驗。
也正因為徐永旭的藝術創作不但是在逾越他自己身體的極限,也將我們帶進一個可以重新定義空間與時間的生命情境,一個可重新找回身體創造力的生命情境,所以我們認為,他的作品既是一種黏土造形,也是一種身體勞動,更是一種生命姿態。這個生命姿態,我們可以稱之為肉身苦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