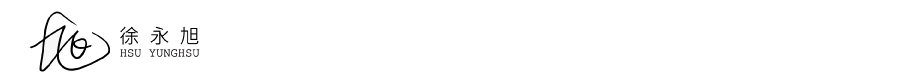走進陶塑的當代藝術歷程—徐永旭陶土創作的三視觀
陶藝作品製作成形中存在著不確定性因子—釉藥本身的化學變化、窯裡氣氛與溫度的游移、土的時間性與成分難控…,這些命運式的機轉,都是影響陶土創作者掌握與表現作品的成敗關鍵,甚至有所謂仰賴「窯神的喜悅降臨」的形容。1980年代末,徐永旭揚棄專業古箏音樂演奏家的身分,從表現抽象樂音的展演,轉而以務實、接地氣的陶土媒材來創作,他對此現象提出質疑:「作品進窯後就交到窯神之手,那還叫藝術創作嗎?」
這個問號,促使徐永旭兌現自己設下的門檻,一開始採取紙上製圖設計的方式,運用了年少就讀雄中時學會的三視圖繪製原型,接下來只要能依計畫步驟按圖施工即成。然而,幾次操作下來便逐漸感到:設計圖畫完,似乎創作也完成了。他曾自問:「這種事先規劃掌控完全的方式像是在produce而非create,我能不能不要畫圖?能不能讓它有些動感?」類似這般的反省與問號,幾度改變他的創作方式,催生出他在藝術生涯的變換與發展上,朝「陶土造形」/ 以土雕塑之路邁進的旅程,以及與土緊密、滲透般的經驗關係。
初次在藝廊空間裡見到徐永旭的作品時,感覺那像是快衝破天花板的陶土身形,發出了「注意保持緩衝距離」的聲音。於是身體試圖靠近的同時,留意矜持,腦中試圖解讀看似複雜無章的抽象結構,卻又著迷於眼前那彷彿可觸及的規律紋理形式,頃刻間陷入沉靜、迷惑又崇敬的境地。在幾次有幸訪談創作者的機會裡,寄望以為能有抽絲剝繭般地尋著解惑的閃耀時刻,殊不知,創作者生命際遇中無數的創作靈光與激盪火花,已如繁星般細密地撒播隱入完成式的時空布幕中。探索徐永旭長而蜿蜒的創作經歷脈絡,三十五年的時空交織匯聚,我試著學習「三視圖」繪製藍圖的方式來分割紀錄,想像時空的維度,以三種觀看的方式進入徐永旭與陶土共築的世界。
第一幕,以速寫素描方式勾勒徐永旭的藝術人生場景,在時間軸中揣摹他意志堅定的抉擇時刻、汗水與收穫的歷程,一個全力專注自我、掌握創作生命發展的輪廓。也藉由他在陶土創作道上所標註的活動記號,讓我們在臺灣陶藝風景的變幻中,追蹤一條穿越現代陶藝沃土,走向當代藝術的林徑。第二幕以似無人空拍機或自動縮時錄影的方式俯瞰、凝視作品,如測量地貌一般在空間游移;透過徐永旭於創作中的身體軌跡,探索泥條從肢體線條中的延伸形塑、由個體單元到結構交織的一統美學。第三幕以切片般的探視,取階段性的公共裝置作品對照當代環境,驗證徐永旭穿越陶土造形藝術的界線,以土建立場域精神,為時代留下壯麗地景的傳奇。
第一幕 徐永旭的藝術人生場景
峰迴路轉
徐永旭原籍臺灣澎湖,1955年出生於高雄。從小即展露旺盛的美術天份,小學經常代表學校參加繪畫比賽,順手拈來就抱個獎回家;另一件貫穿少年時光的事則是「跑步練田徑」。因當時家裡經濟的限制,保送高雄二中(現前金國中)後成為田徑校隊選手的他,一心想考取臺中一中體育實驗公費班,然而就在取得保送資格的最後一哩競賽上鍛羽受傷,終結成為運動家的夢想。荒廢的學業在短時間內得接受聯考的挑戰,他埋首力拚,仍高分考上高雄中學;不料,礙於現實經濟考量,讀了一年只得放棄,選擇重考一年,進入公費的師專。
年少即經歷了一趟峰迴路轉,在夢想與現實的跌宕衝擊中,徐永旭從田徑場上紮實地跑出韌性與堅強,對學藝的執著與專注由此迸發,在往後專事創作的藝術家生涯中,也從未停歇。
1971年進入屏東師專,展開黃金人生的學習生涯。該校的國樂團執全臺灣樂界牛耳,順著校園裡的風氣,徐永旭在社團中很直覺地選擇古箏這項樂器。同時他不忘田徑運動加入校隊,也瘋狂愛上畫畫,常常假日腳踏車騎著,背了畫袋就到郊外寫生;過著像夏令營一般的充實生活。
在徐永旭接觸到陶土,進而積極成為專業的陶作藝術家以前,他的少壯年華是另一場蠟燭兩頭燒的人生。一如他在興趣和天份上的充分追求與開發,為了古箏,曾經下課後北上拜學國樂名師,再連夜搭著野雞車晃回高雄天已破曉,就接著前往小學任教。如此精進成就了他古箏演奏家與授課師的身分,有五場個人古箏獨奏會的紀錄,歷經一段精采的舞臺人生。然而在平日還有小學授課的職責下,當時忙到一個月僅有一日的休假,身心健康幾乎不支負荷,常年練就的體力與腳力功夫全廢,加上古箏同好師長的驟逝,再次面對古箏這項樂器時,徐永旭從身體的覺醒中生出徹悟—1985年,舞臺人生的絲竹笙歌嘎然而止。
來到用土創作的起點 1987-1992
1985至87年間他重拾畫筆創作,教職上一位教美勞的同事找上徐永旭合資開工作室。起先他只負責幫忙練土、準備材料;某次試著自己做了幾個杯子,黏上把手後即擱置在架上,隔天再見時把手全都扭翹了起來,原來是簡便蓋起來的工作室中,從透明浪板屋頂灑露下的炙熱陽光,導致素坯體收縮太快。初次接收到土在不同溫溼度中形質改變的現象,引起了徐永旭學習的興趣;開始自己買書來研究。
他一讀就入迷[1],開始不斷尋找任何與陶瓷相關的書籍閱讀,甚至到外文書店去找、開書單託朋友到美國購書[2];按著電子字典逐字查閱,憑著求知若渴的毅力克服語言隔閡,從紙上獲取關於材料、釉藥的專業知識。有了知識,再次摸到土,彷彿生出一拍即合的默契,勾起徐永旭狂熱的創作慾,讓他能沉浸專注其中,甚至忘了身體多年的關節炎疼痛[3]。
徐永旭也與夫人林秀娘[4]兩人一起向林瑞卿師傅學拉坯,使用瓷土練習,培養出紮實的拉坯技術。1989年徐永旭與合夥同事蓋起柴窯,按設計圖規劃的一室登窯外觀很美,溫度卻燒到1000度就升不上去,投柴時又燙得讓人難以靠近;後來向專家請教與自行檢討後,終於改善成功[5]。經歷了這些摸索,他對陶瓷藝術的世界更加嚮往。1980年代南方陶藝學習氣氛熱絡,留美歸國且從故宮科技室歷練出來,隨夫婿回到高雄深耕的楊文霓老師,開闢了一片陶林。1990年徐永旭進入楊老師門下,從基礎班開始學習陶藝各方面的技法[6]。在此之前,雖然徐永旭其實已有他摸索中建立起來的陶藝基礎,然而跟隨楊老師學習的經驗,讓他有機會在不同的方法學中自我辯證,從而發現一條適性的創作方向。
奮力向前 拓展陶土展演的疆界 1990年代
接下來的兩三年裡,徐永旭參與國內多項重要的美術競賽屢獲佳績—第21、22屆 (1994,95) 臺北市美展陶藝特優首獎,第三、四屆 (1995,96) 金陶獎社會組造形創新銅獎,國內與國外(第四屆葡萄牙亞威羅)的雙年展入選…大小獎項,僅是1995年一年內就拿了七項競賽獎項!如一顆初登場即閃耀發光的新星,但事實上當時的徐永旭已入不惑之年。
田徑場上後來居上而成功的例子不無少見。起步晚且無正統藝術學院背景,常讓徐永旭懷有缺憾,然而他急起直追的奮力與勇氣,令人刮目相看;旺盛的創作能量與生命張力,正好搭上臺灣90年代現代陶藝活動與展演的繁盛列車[7]。造形上帶著亨利摩爾的雕塑特徵,以人生命題、社會批判意涵的現代陶塑風格,在先前多場競賽中早引起眾家注目,高雄的藝廊也爭相邀他個展[8],積極參與多項陶藝聯展後,更確立了徐永旭以陶塑創作出道,進入藝術職場之路。1998年,徐永旭作出了重大的人生決定—放棄教職,專注創作。憑著「已知換未知的勇氣」[9],前去請教多位前輩這項決定。其中,資深陶藝家蔡榮祐老師一句「教書很多人會教,作陶只有你會作。」[10]給了徐永旭很大的信心力量。1999年上半,徐永旭集結了自1994年以來創作的系列作品,以及首對一體成形的變形人形陶塑《王與后》,於臺灣省立美術館[11]展開一場「世紀舞劇」,標誌了當世紀末土之展演的疆界。
遊走創作換日線 一條探索身體與空間維度之路 2000-2010
進入新世紀的千禧年,時局瞬息萬變。徐永旭在造形上的追求遊走於具象與抽象間,尺寸體積也逐漸變高、變大,2000年大型陶塑作品《如皇》、《似妃》,似乎揭示了向公共景觀雕塑藝術靠攏的意向。1999年成立的朱銘美術館座落於金山廣大開闊的山林間,以藝術交流區對外伸出觸角;徐永旭鼓足信心地向朱銘大師提出申請,為他的大型陶塑作品找到理想的展演舞臺—以大自然開放的環境為背景,上演一齣題為「位」的劇碼。劇中,演員們的身體被賦予了「座位」符號,指涉位子、位階、社會地位的關注思考,借隱喻增強了作品的敘事與故事性。
1990年代末,國際間在藝術中心早行之有年的短期駐村或工作營的交流方式,開始在臺興起[12],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成了徐永旭頻繁往來外地創作的時期。一開始,2001同一年中就參與了三處工作營[13]。2002年流浪至中國上海十里洋場欲求新契機,落腳上海樂天陶社駐地創作與教學[14]。2003年,閉關苦讀三個月,考進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跟隨張清淵教授學習。受張老師引薦,他遂開展了一段往返臺、美的異地創作之旅—2004年上半前往美國中西部密蘇里州的歐札克斯學院藝術中心(College of the Ozarks, MO)、2005年東北部紐約州羅徹斯特理工學院(Ro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R.I.T., NY)、2007年西部加州州立大學長灘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ng Beach, CA)。期間徐永旭的作品受到信樂陶藝之森館長的賞識,於2004下半年受邀至日本滋賀縣信樂陶藝之森(Shigaraki Ceramic Cultural Park, Shiga)客座駐村創作[15]。
這些密集的時空變換、駐校駐村時的見聞遊歷與工作狀態,讓徐永旭的視野與創作方向從過往直線性的造物思維轉向外在世界,再鏡射回自我內心與當時研讀的哲學課題、創作手法交相辯證;尤其為2005年旅行中見到美國雕塑家理查·塞拉 (Richard Serra, 1939-) 的大型扭曲、傾斜鋼板的極簡裝置藝術所震撼,啟發他思考作品的空間性與創作臨界的問題;並進一步從閱讀傅柯的生命技術-關注自我[16]中,逐漸形成他代表性創作的當代美學觀念。
2005年從美國回臺後,徐永旭在前往學校工作室的高速公路途上經歷了一場死裡逃生的車禍,為撫平那生死一瞬間的驚嚇餘悸,他想到在R.I.T.創作狀態不佳時,強迫自己以手入土開機的方式:握土球在手掌中反覆推動、壓揉至杯形或船形的片狀,遂慢慢平穩了情緒、卸除壓力[17]。這種以身體作為、身體知覺為先的創作體會,將作品與自身的關係拉到了同一軸線上。而後,透過研讀梅洛龐蒂的「身體感」論述[18],在長時間手指捏塑泥條與感知土的乾濕度、可塑性的經驗反覆積累下,找到身體的界,進而以身體的逾越、創作的逾越-徐永旭的「反陶」[19]創作過程與自我技術中,掀起了全新、令人驚艷注目的陶塑藝術,以極大、極薄的延展,燒結成一座硬度與脆度、穿透與臨界感同具的迴圈,首度發表於2006年碩士畢業展「界.逾越—徐永旭個展」中。繼之,於2007-2008年的高雄市立美術館申請創作論壇展出的「黏土劇場—徐永旭個展」,擴充為以數十座兩米高的帶狀橢圓陶圈排列成如劇場氛圍的空間,讓觀者得以穿梭於如江南庭園中的陶林間[20],感受創作者千指萬揉於陶土中散發的溫柔堅毅。徐永旭以身體知覺、肉身苦行持續操演陶土維度的創作方式,在作品《2007-06》獲2008年日本「第八屆美濃國際陶藝競賽」首獎[21]殊榮後,如跨過陶圈形成的時空入口,踏進了一段當代藝術的進程。
無盡的視野
徐永旭自言,「超越,由生命超越生命,由藝術創作超越藝術創作,由藝術創作超越生命。」[22]回溯他從運動員、古箏音樂家至今以陶塑造形為表現的藝術家之途,一路上生命充滿了張力,而這股張力也透過創作中訴求的「逾越」觀念傳達出來,其力量轉換自他強大的念力,不斷的試煉與征服困難的信心,因著生命突破創作,又因創作突破生命,讓作品標誌著時光印記的同時,又持續一點一滴地在進展衍繹中。
徐永旭的創作長年與泥土作抗阻,推擠按揉土條的手掌經常掛著繃帶,在圈條走泥的過程中,半彎的姿勢身軀也不時地需要包裹護腰撐著。他視哲學為人的底蘊,潛心去吸收鑄造當代美學心靈運作的哲理,並試圖付諸實踐,經「反陶」的勇氣力量,克服了造形、燒窯設備的限制,找到了陶 / 身體的「界」,並且為作品的裝置與移動呈現,超前佈署了縝密的防護措施,這一切,讓他的藝術表現意志能貫穿陶土,將「土」原始又文明的風貌帶上了當代藝術的舞臺。
看著表面由連續手指按捺所留下的紋理,我想像那最微小單位的凹痕是以每1-3秒的速度出現;退後三步才驚覺,眼前歲月壯闊,是幽谷是山川,藝術家的陶土演繹帶領我神遊於無盡的時空視野中。
第二幕 從泥條到陶塑 土貌萬千
人類史上最古老、最個人化且直接的塑形方法—泥條盤築,是將搓成條狀的黏土透過手掌的擠捏按壓,一層層盤疊成器;相較於轆轤拉坏,此法是一項以較平緩的速度,對陶器的大小形狀有更高掌控度的方式,且因著掌握度有助想像造形的開發。徐永旭自始至今都是以此項成形法做為他的造形基礎。
1994 靜態與動態的分水嶺
1980年代末徐永旭成立工作室之初,臺灣陶藝的發展圍繞著容器的現代性藝術表現,在此氛圍中,他以泥條盤築法做了第一件封閉式方體造形物《象》(1990);方體側面中心嵌露著球體,四平八穩的對稱平衡結構中,表面以不同色的化妝土層疊後磨除,顯露出細緻繁複的紋路質感。緊接著,《剔紋大甕》(1991)、《鵠》(1992)[23]、《扣》(1993)[24] 也都是以圈泥盤築成容器,盛載著相同技法的化妝土裝飾,為反動窯神的迷思按製圖設計步驟完成的作品。
但是這種一起頭就掌握全局的方式,漸已不能滿足他旺盛的藝術創作企圖。1994年以兩件不同造形手法表現的創作《滴》與《白色樂章—舞》,一起參加了臺北市美展;作品《滴》獲得了陶藝類特優首獎,柔和婉轉的外形與層層顯露的溫暖色彩讓人耳目一新[25],但其實這樣的表現與創作過程,仍是在製圖計畫中的步驟下所執行的封閉器物造形,它是嶄新的起頭同時也是結束;徐永旭放手一搏地朝僅得入選的《白色樂章—舞》作品方向繼續發展,從舞蹈般的旋轉中自由、開放的延伸出去,開啟作品動態,也開啟了一座以土展演的舞臺。
舞.舞.舞
從底部的圈泥條逐層往上發展時,身體自然地帶動著腳步與手繞著作品旋轉,以一種連貫的韻律向外向上扭動、延伸,漸漸地人體概念進入器形;宛如手臂張揚,也如人的舞姿妙曼。作品如《白色樂章—共舞》(1994)[26]、《夜舞》(1994)[27]、《精靈之舞》(1995)[28]、《永恆的舞者》(1995)[29]、《舞臺上的人生》(1995)[30]有著各自的舞碼,也有相應的結構與肌理特色。1994年徐永旭第一次在高雄的書店看到英國雕塑家亨利·摩爾 (Henry Moore, 1898-1986) 的專書,為之著迷,「斜倚的人形」進入了他的腦海印象裡,從他盤泥的手中抽高,僅以三支腳鼎立繼續他的旋轉舞結構,直到曲終收尾,泥條是該切還是續接,成為當時面臨的一項造形課題[31]。
此外,表面質理則呈現兩極化。當時取得的材料不甚穩定,於是徐永旭自行配土實驗,每件作品配不同的土來用,為了展現土質肌理與希望的色質;作品《夜舞》即是首件以熟長石顆粒凸顯陶土材料肌理的作品。另一方面,此時創作心態上,對於表面的處理又希望不見陶瓷技術的痕跡,不留工藝操作的影子,因此會先上化妝土後表面予以打磨,使其看起來光滑無孔;例如作品《共舞》(1994) [32] ,甚至一度在《白色樂章》系列作品表面上漆,凸顯思考作品永恆性的問題。
1996-2000 戲劇人生
從旋轉、自在的舞蹈造形中,徐永旭逐漸走進大眾的視野,隨著得獎與展覽機會愈多,取悅視覺的表現也增強,顯現在結構險奇或是造形曲折幅度迴旋誇張的作品上,如作品《共舞生涯路 》(1995)[33] 、《精靈之舞》(1995)、《共舞人生 (二)》(1995)、《戲劇人生(三)》(1996)皆為兩段式組合的結構,以「倒影式的基座」[34]拉高作品視線,營造出具有戲劇性的驚險動勢;作品《煉》(1997)、《擘》(1998)發展出像舞者手持的彩帶線條旋繞飛舞,也形塑出抽象音樂的高低旋律與快慢節奏,具流動與穿透性,在視覺想像與意境體現中顯得氣韻生動。
除了上述營造戲劇、動態的線條與結構,1997年起,徐永旭使用的造形語彙愈趨具象與豐富了起來。作品《風雲際會》(1997) 中,一只面具被拱起,四周環繞著魅影般、頹圮殘存的柱子,召喚出古希臘戲劇誕生的雅典劇場印象;一改先前的三足鼎立結構,《王》與《后》(1998)首以四腳座椅結合西洋雕塑中裸體軀幹的形體,並與予解構地在身軀留下空洞,加上從意識創作中而生,帶點詼諧趣味的圓坨水滴造形大腳。面具(金箔化妝的面具與非洲人面容特徵的面具)、乘載面具的錐狀柱、擬人化的大腳、座椅,這些符號象徵交相混合在此時期的作品中,讓金箔與呈現自然土色的陶塑形體,充滿著原始色彩與神祕性。2000年的大型戶外陶塑《如皇》、《似妃》可謂集大成,以形式化的人體軀幹與座椅結合,人體面部繪有「戲劇人生」系列的金色面具,雙手垂放於膝上,宛如古埃及法老雕像的莊嚴神秘,座椅下方的檯座側邊則混搭了非洲面具的裝飾[35];在混合時序邏輯與意識、意象的拼湊上,烘托出超現實主義劇碼「位」,訴說著人世間關於位置、權位、地位的寓言。
自1990年代早期從器物創作中灌入了人形舞蹈之勢,徐永旭的創作思維一直環繞著對人體的關注,以及回應生命中曾有過一段登臺演奏的舞臺人生。在跨世紀之初出現的巨型陶塑《如皇》、《似妃》,結構形式可推溯至「舞」、「戲劇人生」兩系列中使用的「倒影式基座」,經過數次的銜接應用,進擊成為豎著腳跟或圓坨大足的座椅。座椅暗示著「邀人入座」的姿態,然實際整體形體因座椅基座變高變大,樹立起作品與人之間的張力;一方面為戶外廣場的廣大空間所期待,一方面也進入了公共藝術領域,接受觀眾的挑戰與解讀。
變形—分裂—逾越
新紀元裡,徐永旭開始參加各地的工作營並且到了上海駐村教學。在異地而作的環境中,一方面調適當下的心境與工作環境,一方面在靈感造形的探尋中不斷地創新、整合;經歷一場動盪不安中尋求突破的過程;此時,「神話系列」的出現映照了這樣的心境。
除了創作上直觀的反射心靈狀態與環境,徐永旭指出,「材質、造形與質感上的對比能同時在一件作品上出現,是我稱之為神話的緣故。」[36]而希冀此狀態的發生,更早可從作品《越》(1999)、《協議》(2000) 觀察到一種「變形」[37]力道的開始,表現流動又凝結的釉質感,分離卻又相互支撐的結構,是他在材質與造形上企圖突破的思考,最終完整體現於作品《神話-8 》(2001)[38]上。在圓雕造形範圍內表現形體變形、分裂的狀態;上端似獸頭也是萌芽,下方非足而是滴流,在亮釉有機曲線vs. 岩質稜角的對照中,在斷裂流動的永恆捕捉中,嚮往與羈絆相生。
2003年徐永旭考進南藝深造,在當代藝術學風的主導下,重新建立與檢討創作思維;誠如張清淵教授引導他丟掉過往包袱,展開新做法的路徑—「從原來的想法中去改變造形,再從造形裡去改變想法」[39],首先進行的就是解構、崩裂;從2004年在美國歐札克斯學院藝術中心駐校創作的《神話2004》系列作品中開裂、分裂出片狀,一步步愈趨向無人體線條暗示,完全抽象、打破敘事的造形,以《2004-10》標幟出創作意志改變的過程展現[40]。接著,徐永旭寄予片狀形體空間維度上的思考,嘗試將物象的能量透過高飽和度色料化妝土的應用,以色光、光暈的形式微微透發出來,向盧奇歐.封塔納 (Lucio Fontana, 1899-1968) 的空間主義致敬。
2005年春,徐永旭前往美國紐約州羅徹斯特理工學院擔任駐校藝術家,在州內旅遊期間前往迪亞貝根藝術基金會 (Dia Beacon Foundation) 參觀,見識到三位空間裝置雕塑藝術家的作品,給予他相當大的震撼。理查.塞拉[41]的大型鋼板裝置,斜傾卻能不需支撐站立,抽離任何關係卻宰制觀者空間知覺;弗瑞德.桑德貝克 (Fred Sandback, 1943-2003) 以織線在空間中作線形切割,定義了觀者對虛擬空間的感受;麥柯.海瑟 (Michael Heizer, 1944-) 在展場空間地上製造出四大深坑(命名為東西南北),吸引著觀者好奇的同時又讓人產生身體上的警戒。這些藝術家以當代藝術創作的代工工序傳遞的極簡特徵,抽離了人的關係,卻激發觀者的身體空間臨界感,啟發他思考:創作者如何突破媒材限制?如何讓觀者進入作品的維度產生共鳴?[42]進而在他接下來的創作辨證上發酵,引領他接收梅洛龐蒂以身體為主體的哲理,覺察人的「身體」作為衡量與感知作品尺度的方法—以徐的創作來說,即是以自己的身體經驗,重新詮釋了遠古自有的「泥條盤築法」—從原來的知覺狀態溢出,嘗試不同使用手的方式進行泥條捏塑[43],打破身體經驗的慣性,達到最終和諧規律地讓指痕烙進土的肌理,成為他個人獨特的語彙。
2006反陶
從身體到創作上的逾越,徐永旭進入傅柯的「生存美學之自我技術」中,以自我錄影的方式紀錄檢視創作狀態,讓自己保持在脫離慣性的警醒態度,採取脫離傳統的作法,在圈泥的起始中跳過底面的支撐結構,直接構築邊牆,並在保持牆面一致薄度的環境下,盡其所能地延展前進,造形走向極大、極薄。又採如「走鋼索」般地實驗,將過往認為安全的結構因素抽去[44],從失敗坍塌的碎片中找出可能或無法繼續的成因…,作品介於成與不成的臨界點。
徐永旭稱經由此過程而成立的作品為「反陶」—「我並不是要顛覆它本身或挑戰所謂的極限,而是取用了它傳統優質面的相對性,視它為相異於陶的陶,將它定義為反陶。」[45]
一般對於傳統陶瓷的認知是堅硬安穩的材質,以追求表面的光潔無暇技術,分工或獨立而成;徐永旭在2006年開啟的「反陶」經驗,可說是個人情感意志與陶土材質特性的一場搏鬥。在陶土極大極薄化的過程中,手掌與指頭不斷地擠壓、捏塑,身體的勞動重覆堆積,同時對抗著堆疊中的重力、環境微氣候中陶土乾溼物理性變化的考量,心境也隨著節節起伏;讓下一單位的泥條在作品皮革硬度之前持續地銜接加高,是創作者身心上的考驗,廖仁義教授深刻的比擬為「春蠶吐絲」,一種在媒材與藝術家身體之間,存在類似血緣關係的「肉身苦行」[46]。高溫素燒後,陶土縱使產生硬度也伴隨脆度,在佈滿著個人不經修飾、毫無掩蓋的指痕中,沒有上釉的陶土粗曠自信地吐露著千年輪迴於大地中的礦物氣息。
當走泥結束,龐大的土象迴圈[47]在人力與機械運作的拖吊拉等合力下進入窯體燒成,收縮龜裂的不確定風險令人忐忑;當作品進入了空間,以90度的翻轉,成功告別橫向運作的過程,新的視野讓作品於焉成立,反陶的創作最終拓展了陶瓷藝術表現的疆界。泥土,代言了徐永旭個人的精神意志與情感,使材質與創作者同時成為無法被取代的唯一。
土貌萬千
2005年美國 R.I.T. 駐校創作期間,徐永旭面臨一種停滯不前與壓力增生的狀態,在內心的衝撞中生出手的自動性技法—下意識地使用小土球於手掌心中揉捻出碎化片、杯狀的單元物,直至後來回臺經歷車禍,再次以小單元的土球揉捻排除了受創後壓力;於是,「小單元」碎形杯狀物化為這些經身體驗的見證,成為繼線性迴圈的結構之外,另一項形塑土貌的語彙。
2009年「再—徐永旭雕塑個展」中,首次展出以重複性碎化片狀的「小單元」[48]作堆疊、擴散、融合成可大可小的繁衍體,它們在從容互擁中彼此讓出不同的間距,生物性的群聚佔據一方或排列鋪陳上牆,彷彿地衣般的延展附著於大自然各角落。「周流.複歌—2012徐永旭個展」中,生物量能的趣味更加突顯,編織、結締狀態更加繁複蔓延,形成如珊瑚礁、巢穴的陰性空間;如龔卓軍教授指出,「在陰柔的繁衍美學與陽剛的逾越美學兩種創作風格之間,徐永旭進行了更多的相互滲入。」[49]直至2018年的「大器逍遙」展,展中首次出現了繃帶式的薄長土片,它們覆蓋、纏繞或包裹著眾「小單元」們,與這些聚合起來的「孢子」或「樹蛙卵泡」[50]、「錦簇的花叢或茂密葉片」[51]、「脫落的稻米外殼」[52]…串連交會,形成如樹林枝枒或森林路徑一般的生態地景視界;又如2020年「徙越」展策展人徐嚖壎從徐永旭的跑步習慣,形塑出鮮明的觀察:寬長的薄土片與其下的「小單元」們,形成了主要道路與羊腸小徑、螺旋梯所構成的阡陌縱橫,像是藝術家旅途中的移動視野或邀請觀者一同參與的心靈秘境[53]。
第三幕 超以象外 地景中的陶
自2007年的「黏土劇場」以劇場氛圍展演開始,無論是在臺灣主導當代藝術發展的藝廊場域,或是在公共環境藝術計畫中,徐永旭的陶土創作持續朝向裝置藝術的方式思考,將整體空間、觀者納入作品展現的凝視範圍中,透過作品與空間維度的多重互動,邀請觀者以己身身體經驗參與。事實上,早在2000年朱銘美術館中展出的「位」系列作品,就具有這種當代藝術形式之戶外活動的特質。
徐永旭於南藝研讀時期,幾乎都會做塞滿窯體大小的作品,他曾說「窯有多大我就做多大」[54]。由此可見窯體在陶土造形創作的重要性,窯體尺寸參與了創作者的身體感與作品空間的臨界感,也說明他以「工作室作為藝術家身體」的概念[55]。2009年因參與「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歷史文化公共藝術設置案,找到了目前位於官田的工作室空間;直至2014年因新加坡Select集團建案新增兩大座窯體,形成今日四座共58立方尺體積的瓦斯窯狀態,堪稱亞洲個人工作室規模中最大窯體。
這兩階段的擴增巧妙地與他的作品公共化有所關聯;從窯體空間到戶外空間,公共藝術或戶外裝置作品是徐永旭與世界連結的一項轉換橋樑。從製作、運送到定點裝置,這項浩大的工程集結了人力、機械、科技、藝術,讓作品順利進入自然空間,在這人為主導、定義空間的過程中,「土」這項媒材透過窯燒轉換為「陶」,蘊含著土質肌理與徐永旭的指痕,不僅是他個人藝術見證的分身,也透過陶土造形藝術識別進入與人文、自然、土地結合,讓作品與群眾有最近身的交流相會。
與自然相接
在「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的計畫中,因安平港特殊的地理位置,每年的西南季風吹起,沿岸地區會因為風跟海浪拍打形成海濤鳴叫的聲音,當地人稱「南吼」[56]。徐永旭以此歷史知名的地理現象「安平海吼」為出發點,為園區的觀夕平臺設計製作了兩座直立迴圈的陶土造形作品。以及擴大兩件手捏塑時所產生的指痕肌理土形創作;同時也邀請在地社區民眾前來參與手痕壓印於陶板上,作為階梯鞍馬區上的陶板裝飾。藝術家與民眾的手指印記,藉由陶土,在此逾越時空相會。
兩件直立式迴圈陶作的設置,有兩項特殊的考量:其一,開口朝向海邊,當風吹進來時與陶板形成共振,觀者如果靠近作品,猶如撿拾海邊的貝殼靠近耳朵,頓時屏除了現實世界中的吵雜,將可聽到更清楚的風聲。另外,季節變換時夕陽落入海面的角度與光之軌跡也跟著移動,結合這項大自然造化之功,作品的擺設方向讓並排的陶圈孔隙,剛好對上每年冬至、春分、秋分時太陽落入海面的軌跡,美麗的夕陽光線穿越作品,捕捉永恆於瞬間。
與現代交手
另一項與建築師陳家毅先生合作,為新加坡SELECT 集團所屬餐飲大樓設計的建築外牆裝飾,是徐永旭從己身創作經驗與設備評估下大膽挑戰的業界建案。陳家毅建築師為大樓外牆賦予了竹蒸籠的意象,希望在今現代任何事物皆可被複製、生產的環境中,還能有一種傳遞人文溫度的媒材表現,而徐永旭具手感的陶塑方式,正好回應此一當代環境的叩問,讓這古老又親近人的媒材—土,再度甦醒於現代生活中。
幾乎是不惜成本地擴充了工作室設備:兩座20立方尺瓦斯窯、大型練土機、大型陶板機,大量訂製的大尺寸硼板、高達86公分的硼柱等,加上燒製中變形、破裂、運送中損壞的不良品成本,難以估計;另一方面,他土法煉鋼的設計出一些能訂製化、量化,搭配人力調整的簡單機具,例如:練土機出土口上方加裝分隔鋼板,讓練出來的管狀陶土破開,並在工作人員的裁切下順利攤平為陶板;接上陶板機輸送至曲面木造模具上—由人工手動的移動式吊掛鍊條承接,使陶板在曲面木造模具上方便整型、運送…等。這種如達文西造物、米開朗基羅以藝術為建築服務的精神,讓徐永旭工作室裡的生產動線運轉起來,一切就緒地與建築的精準現代性交手。雖然起先不安地認為承接此計畫是「一項災難的開始」,然終究在他獨具毅力、眼光的領導,與陶土造形的經驗值運用下,將從美國前後進口240噸、17貨櫃的土,歷經整整一年的工期窯燒,成功地完成每片重達90公斤、厚度3公分,曲面造形長2.1尺、高75公分、深約55-60公分,共2500多片的曲面陶瓦製作與出口。
徐永旭以藝術創作的思考模式接下了產業的製作,他深知必須配合建築上的規畫設計,作跨界的銜接,使成品規格達到業界要求的標準;同時又在陶瓦曲面上直接以手指推畫線條,作為他個人的藝術識別象徵;因此,從產業訂製角度看來皆同的每一片陶瓦,其實並不完全相同,容許一點非完美,以有變化的重複勝出於工業化的精準重複。在陳建築師的構想中,徐永旭的創作模式、陶土藝術,間接形塑了當地環境的場域精神—讓該地域中的文化、社會特徵重組提煉了出來,成為亮點。
公共裝置作品落實了徐永旭身體感知空間的美學,讓身處自然環境中的人們,感受到作品獨一無二卻又能親近的存在,如同有生命時時在變化,也時時在創造中。從泥條到陶塑,逾越、滲透土的臨界,引領陶土藝術走進當代藝術歷程;我們見證了陶中有地景,土貌萬千;地景中的陶,超以象外,盡在徐永旭的藝術視野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