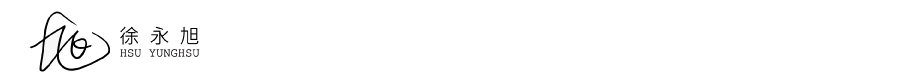身體的韻律;宇宙的形體 (The Rhyme of Body and The Shape of Universe) 向永恆、無限開敞的徐永旭
資料來源:
右圖https://www.pinterest.com/pin/393079873702771134/
左圖https://www.pinterest.com/pin/521854675543737833/
下圖徐永旭作品
前言
所以有的信仰、藝術及科學乃是同一株樹的分支。上述種種切望總是朝著提升人類的生活,將生命從僅僅是物質性的存在提升起來並且引導個體朝向自由(“All religions, arts and sciences are branches of the same tree. All these aspirations are directed toward ennobling man’s life, lifting it from the sphere of mere physical existence and leading the individual towards freedom.”)_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科學與藝術二者,都和將紛亂導入秩序有關“Both science and art have to do with ordered complexity.”__萊斯洛特·羅·懷特(蘇格蘭工程師;未來學家Lancelot Law Whyte)
上列三張圖片中;右上及左上的圖形是拓樸學中極為重要的一個形體,這個猶如孔洞鑽竄而成的形體,稱為「卡拉比–丘流形」(Calabi–Yau manifold);也叫做卡拉比–丘 n-流形。它的誕生歷經了一個天才數學家(卡拉比(Eugenio Calabi))的初始想像以及另一個天才數學家(丘成桐證明)的證明,從猜想到證明完成共計花了20年的時間,這個視覺形態上,看似徐永旭作品造型單元的形體,才真正被科學家所完成。
「卡拉比–丘流形」除了在三維視覺空間中看起來與藝術家的作品造型單體很相像以外,這個名稱拗口的形體,還對當代理論物理學的時尚學說「超弦理論」有著高度的重要性。在「超弦理論」這個專門用來總括、一致的物理理論框架,能夠解釋宇宙的所有物理奧秘的萬有理論候選理論中,「卡拉比–丘流形」被用來在「超弦理論」的十一維空間的模型中,保持宇宙的超對稱性不被破壞。
由於「卡拉比–丘流形」看似猶如藝術家作品的造型的單元,也因此徐永旭的創作巧合地和「超弦理論」這個最先進的宇宙形態猜想,在拓樸的不變性中相遇。一如愛因斯坦以及萊斯洛特·羅·懷特這兩位最早從事萬有理論的科學家所言一般,科學與藝術乃是同樹異支,他們朝向真理生長,並給予世人對於這個複雜的世界一個具有秩序的洞察。
從冶陶的身體韻律到拓樸形態上的宇宙形體,徐永旭的藝術實踐,一如其傳奇且帶幾許著英雄性格的藝術創作生涯,持續地自我挑戰與突破,並朝著永恆與無垠的時空想像而去。於是我們當我們凝視作品並觀看與丈量藝術家的想像界時,那美感的體驗性也因之綿長而浩瀚。
一、拓樸不變性與美學不變性
如果要找出一門在當代美學、哲學的理論中激起漣漪的高級數學,那麼拓樸學及其專用名詞(拓樸、流形、平滑、緊緻、鄰域…等)對於當代哲學及美學理論的影響,肯定遠遠地超越其他數學學門。從拉岡、傅柯到德勒茲等法國思想家,對於拓樸學名詞和概念的大量引用、轉介…,讓拓樸無疑地成為了,當代哲學及美學思想中十分熟稔卻又陌生的名詞。在數學裡,拓撲學(topology)或意譯為「位相幾何學」,是一門研究「拓撲空間」的學科,主要研究空間內,在連續變化下維持不變的性質。
姑且不論這些法國思想家是否真正的理解過,嚴格數學意義上的拓樸學,真正值得注意的或許是拓樸所探索的乃是在持續變化中空間的「不變性」。正是這個「不變性」的承諾與探索給予了人文學者一個對於精神永恆性的新想像和新可能,也正是因此當代哲學美和美學探索者才會在,對把握一個單純的數學定義可能都難以掌握的情形下,無謀而勇敢的去嘗試把握,拓樸對於「不變性」的承諾與探索。
撇開拓撲學奠基人龐加萊(Jules Henri Poincaré)及其後數學家對於拓樸的開展、探索與思考。而將注意力集中在「拓樸不變量」這個概念上,在拓樸學中,一個拓樸空間所包含的體積、面積、長度等量並非重點,而是在乎這個拓樸空間所擁有的內稟性質,而拓樸不變量的定義便是:兩個同構的拓樸空間之間相同的內秉性質(著名的咖啡杯和甜甜圈對拓樸學數學家是一樣的,就是一個典型的拓樸不變量。)。如果說「拓樸不變量」乃是關乎空間形態內在本質的恆定性,那麼我們或許可以說正是在這個空間內在本質的恆定性上,藝術造型的美學和數學的抽象思維產生了奇異的共鳴。
正如同前面所舉出的「卡拉比–丘流形」和徐永旭作品中的空間模組,有著高度的相似性一般。徐永旭的作品總是給予觀者一個儘管形體外貌總是處在持續流變的界域裡,但作品的內稟美感卻始終蘊含著共通的「不變性」特質。而我們或許可以說,徐永旭的作品讓拓樸空間的形態和藝術造型上美感體驗上「不變性」有了一個美妙的相遇。
二、身體/技藝/美學
若從藝術實踐的過程來看徐永旭的創作,可以說其藝術不僅總是「身體」的藝術,更是「身體技術」的藝術。一方面,在藝術家整個創作生涯中「身體」始終是一個持續的主題,另一方面徐永旭的藝術實踐跳脫了以「形體」的身體為主題,而轉向了「身體技術」的形體,正是在這個對「身體」形態解放的過程中,徐永旭讓早年深刻的音律教養,轉而成為一種絕對獨特的「身體技術」。而這個獨特的「身體技術」美學,或許還要回到傳統的莊子思想中。
關於「身體技術」,《莊子》書中記載的技藝現象頗為豐富,例如:庖丁解牛、呂梁游水、梓慶削木、痀僂承蜩、列子射藝等等。莊子從這些技藝中看出在獨特的技術實踐過程中,「身體」意象、或者「身體感」所引帶出的肉身「體知」狀態,在審美上的價值。莊子認為真正的身體技術乃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這種技藝的核心狀態為「忘」。「忘」是原本因意識、知見所造成的身、心分離、物、我間隔的狀態,在透過身體感的再三重複實踐後,契合為一,而且這種合一是在身體的技藝實踐中自然而然流露出,完全不必再有心意識的指導作用,這種「以身化心」的身體記憶、自發運動便是「忘」境。因為「忘」境完全不在技術層次的有為,反而只有將任何自我意志的技術有為都放開後,成為一具完全敞開的身體,讓身體成為純粹的通道,此時身體完全與整體韻律融合,由此達到技進於道的妙境。
從《莊子》的觀點回看徐永旭的作品,則可以發現作品上那層層疊疊的壓印痕跡、那揉靭轉折的形體蜿蜒,乃至於那宛若真菌植物般堆疊、蔓生的組態,在在地回應著創作者的身體律動和呼吸,與此同時陶土所留下的不僅是藝術家的身體技術紀錄,這個身體記錄更包含了藝術家與每一個構成單元之間的互為關係,並且身體運動與形式的創造,融合一體。更有甚者,其融合了整體生命場域中的事物存在。正是在這種互滲融貫的體知感開啟中,徐永旭的藝術創造開始從「身體技藝」的美學形式,漸次地朝向《莊子》那「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那逍遙的無限敞開。由是其藝術創作過程變成了以整個宇宙自身為融合對象,身體融入沒有邊際的宇宙自身,從而在作品中透顯出宇宙存有和藝術形式美學二者間的冥契性。
正是在這個絕對開敞的身體技術及肢體律動中,藝術家在作品中構造了那高度抽象的宇宙空間形態。
三、小結
藝術依然是那個可能說出真理的方法
Art remains the one way possible of speaking truth._羅勃特·白朗寧(Robert Browning)
藝術的天職是在藝術性的感覺構成形式中揭露真理….
“art’s vocation is to unveil the truth in the form of sensuous artistic configuration,…”__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G. W. F. Hegel)
望著徐永旭的作品,在穿越蔓延的空間中,藝術家無心卻巧合地揭露了「卡拉比–丘流形」這個數學真理的三維視覺形態,於是拓樸空間裡的「不變性」在徐永旭的作品中,透過藝術家那莊子哲學「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的「身體技術」和美學的「不變性」巧妙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