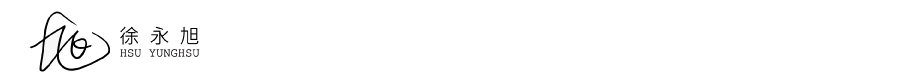關於如何從一成為多:寫於徐永旭2015年個展「Helios旭HiOK」前
儘管曾經在南藝大校園看過徐永旭2006年後轉型的大型創作,卻一直沒有機會認識這位藝術家,直到最近因為在双方藝廊的個展,我們在畫廊碰面,在畫廊的一間小型會議室聽他談歷來的創作,雖然大多時候我們都是盯著螢幕觀看他鉅細靡遺的個人網站,我卻很難不對藝術家談論自己作品的「方式」感到動容,但與其說打動我的是他誠懇的態度,不如說是在描述這些困難重重的創作歷程時,他表現出了某種間接感,像是帶著一定的距離在進行某種對自我的審視,這種距離當然不是因為藝術家特別的理性,徐永旭的藝術語言有著充滿力量的感性,但言談間他的感性卻非常的自我節制,在整個訪談過程中,我們沒有觸及什麼炫目的評論術語,他只是樸實地讓我知道他創作過程的演變。
徐永旭的創作過程演變,大致符合廖仁義曾以西方藝術史流派概念來進行的階段界分:(一)1992年至1997年「生機主義」、(二)1997年至2004年「超現實主義」、(三)2004年至2005年「抽象表現主義」、(四)2005年迄今「過程藝術」。[1]
概括的說,在1992年至2004年的前兩個階段,徐永旭的藝術造形偏重現代主義式的簡化,這些簡化的造形大多傾向有機體型態並夾雜若干符號性思考,這些特點雖然十分貼近臺灣現代雕塑發展的基本走向,但值得注意的,相較於「1985年中華民國現代雕塑特展」引起一波熱議的諸如「台座」等現代雕塑議題,80年代中才轉向視覺藝術的徐永旭,似乎未曾受到臺灣這段時期「現代雕塑」論述的太多影響,尤其隨著林壽宇返臺影響了一批藝術家開始關注「特定場域」等裝置議題,這個時期的徐永旭卻並未在作品的形式框架上有太多著墨,相對的,在這兩個階段中,徐永旭的作品反而隱含了某種社會性思考,就內容來說,這個階段的創作與臺灣當代藝術90年代的代表性團體「臺北畫派」還來得較為親近。
然而,當我們在進行這種比較時,也才意識到這種比較是基於將徐永旭的創作直接地當成雕塑所致,但就藝術家所使用的媒材來說,陶這種材質在學院分類系統中一般偏於所謂「工藝」,當然,徐永旭的作品很難讓我們發現任何專屬於工藝的目的性,但也是在這個「以陶土為材質卻不那麼陶藝」的間距中,在這個被藝術家命名為「反陶」的間距中,[2]廖仁義提及徐永旭的作品時才不得不自造出一個複合性的概念——「陶土造形」,正是這個難以定位的困境讓我們獲得一把關於徐永旭創作的鑰匙,一方面,存在著以自主性為基礎的藝術軸線,從80年代接觸陶土開始,徐永旭便循著一條恪守特定材質的藝術之路,驅動力無非來自現代主義式的自主性想像,然而,就像前述與臺灣80年代「現代雕塑」的論述落差,這種囿限在特定材質並不斷質詢其極限的現代主義路線,卻又同時隱含某種社會性關懷,在這看似互斥的矛盾中,我們幾乎可以說,在徐永旭早期的創作中,那幾乎被遺忘的作為工藝的「陶」本身便意味著一個與自身定位的關鍵性間距,這個間距也同時顯現在他與「現代雕塑」論述的差異中,徐永旭在這兩個階段的創作中,與各種可能的座標始終保持著某種等距關係。
然而,當我們將這樣的間距放在一個更大的背景中,卻會發現,脈絡性的比較多半就已經注定了間距的產生,當1985年臺灣藝術圈瀰漫著一股對於雕塑台座的論證熱情,遲至1995年連德誠才著手翻譯了羅薩琳.克勞斯(Rosalind Krauss)的《前衛的原創性》,[3]其中當然也包括對現代雕塑脈絡而言極為重要的文本:〈擴展場域中的雕塑〉,該文則早在1978年便已完成,而文中述及的極限主義創作泰半完成於1960年代末期,其中也包括徐永旭2005年在紐澤西見到迪亞貝根基金會(Dia: Beacon)的永久收藏——李察.塞拉(Richard Serra)的巨大金屬構成物,這一系列作品對徐永旭往後的創作有著深遠影響,從一個全球化的、在這個藝術脈絡之外皆屬例外的帝國之眼來看,這種間距或可視為陳傳興鑄造的「延遲現代性」的顯著例證,然而,如果說與西方現當代藝術脈絡的比較總是意味著不可避免的間距,或許我們應該尋求的視野將會轉向另一種看待脈絡的方式。
或許我們將觀察的重點從西方藝術史參照稍稍挪開,而專注在徐永旭個人創作脈絡的延展,其中,有兩個特別值得強調的特點,分別涉及個人藝術史脈絡的建造與特定議題的創作思考方式:首先,當與西方藝術脈絡的間距已無可避免,個別藝術家的創作脈絡幾乎已可以等同於一種個人的藝術史創造,這也意味著「參照」總是帶著某種自反性,而根據廖仁義的分期方式,在前述兩個階段後,徐永旭之後進入了2004年至2005年「抽象表現主義」與2005年迄今「過程藝術」階段,藝術家也從偏重作品的完成形式轉向主體性思維,這種趨勢雖然與西方現當代藝術史的發展極其類似,但也是在這個深具自反性特徵的脈絡觀點下,主體性思維才得以進入第二個特點,也就是特定議題的思考方式,被引入的議題是身體。
以2004年至2005年「抽象裂片」系列而言,誠如廖仁義所言,雖然這是一個作品量少也較短的階段,但是在藝術家的創作脈絡中卻有十分關鍵的地位——一方面是風格的變化,「隱喻性的肢體」逐漸消失,[4]取而代之的是抽象卻缺乏完整輪廓的造形,這些作品更像從某個整體擷取出的斷片,如果說過去密封在完整作品形式中的時間性趨近於永恆的古典時間,這些斷片形式卻浮顯出轉瞬即逝的速度感,時間不再彌封於作品內,而是讓作者的介入得以被感知的外部時間,這種看待時間的美學現代性無疑削弱了主體自以為是的能動性,或也驅使徐永旭往後的創作浮現出一股身體與媒介之間相互交滲的不確定狀態,「陶」與其說是作品的客觀材料,不如說是藝術家與藝術間的一場無止盡搏鬥的憑藉,當媒介與創作主體間的界線趨於模糊,兩者間就會形成一具或多具身體的流變關係,時間碎裂在每一個當下的無止盡搏鬥中。
正是在2006年後乃至現在的這個階段,出現了龔卓軍所言的「大孔竅」與「小孔竅」系列,抑或胡朝聖的「大單元」與「小單元」等並行的系列——這些系列不再有明確的形體或符號性的意指關係,而是一個又一個巨大單體的系列性並置(大孔竅),或是由眾多小單體堆疊而成的大型量體(小孔竅),後者有的平鋪於地板,有的則如畫作般懸掛於牆面,這些創作一方面更挑戰了陶土燒製的技術條件,另一方面,也將藝術家在製作過程中付出的身體勞動逼至極限,以致於眾多評論皆聚焦於做為創作主體的徐永旭在創作過程中所凸顯的勞動身體,並由此生產出某種感性詮釋——實則,在面對徐永旭在2006年以後的巨大陶土創作時,當觀者在巨大規模的非人性中卻看得見每一個細節皆為藝術家以手捏製完成,這種以勞動換取的巨大便帶來了某種不無落差的崇高感。
這種落差,一方面意味著一種從底層往上的主題性翻轉,再者,卻也讓我們得以窺見徐永旭的巨大作品與其所心儀的極限主義間存在著某種意願性的差異,因而彌補了「延遲現代性」所指稱的負面差距,另一方面,在這個當我們思考脈絡時便已注定的間距中,除了仰賴創作意圖的差異化,更重要的是這當中出現了「身體」,卻不只是令人感動的勞動身體,由於身體總是並置著私人與公共的雙重狀態,這裡的身體所創造出來的實則遠遠超過藝術家與作品間的勞動關係——儘管就勞動這個面向來說,它是公共的,但也不單單意指藝術家投注於陶土的情感狀態,就這個面向來說,它是私人的。
正是在這個介於公共與私人的身體層次中,我們才能理解「大孔竅」何以總是多個並置,而「小孔竅」又是如何由單體匯聚成形,觀看這些陶土創作,有時我們會覺得彷彿置身一座由不知名有機體構建的微型城市,每一個單體的凹槽皆如巢穴般提供了安頓的私密條件,但它們當中的每一個卻又總是與另一個形成為集體性團塊,它們的有機體構造又系列性地傾向無人稱,它們並非身體的某種隱喻,所有這些造形物本身就是無主的身體,它們是或不是徐永旭的身體也不再重要,如果說它們不是個人的,當然所有權也無從歸屬。
這些身體之所以為身體,正因為它們早已跨越規範了媒介的約定俗成價值,我們唯一能判定者,是身體就如同陶土般為藝術家所用,但兩者間卻沒有形成單向的支配關係,毋寧說,這三項元素——「藝術家—身體—陶土」形成的是一組異質同構的連動軸線,它們相互流變為彼此,藝術成為生命形式,這也難怪徐永旭會深受晚期傅柯的自我技術所啟發,發明自己的勇氣早在他放棄古箏轉向陶土便已顯現——但我以為,在思考徐永旭作品的過程中,涉及自我技術的詮釋雖然迷人,卻也留下諸多謎團,所有這些有意或無意的間距構成詩一般的謎團。
當徐永旭的陶土創作很早便擺脫了工藝性質,卻在進入藝術作為生命形式的現階段,讓所謂「作品」不免再度裂解為基於另一種目的性的「藝術文件」,[5]另一方面,當我們觀看他的作品,又確實就如其心儀的極限主義物件,這些往往十分龐大並拒絕指涉的物件一如以往逼視著置身其間的觀者,在場感,也是在這空無場域中任何感知主體必然遭遇的(藝術)情境,[6]但徐永旭的在場感何以既著重於生命過程的顯露,同時又能顧及最終的形式完整性?較諸1985年林壽宇的極限主義,身體與物之間指向的是毀壞之必然的共同命運,[7]卅年後,徐永旭的陶土創作所凸顯的在場卻像是某種生命的「過量」,創作者的身體勞動過量,而創作本身也毫不避諱地任憑一成為多,這是一種將生命的無端耗損視為游刃有餘的過量,正因為耗損,所以倖存,正因為成為多,它不再局限於徐永旭自己的事,這或許也是在聽他描述自己作品時,我始終感受到間接感的原因吧。
[1]見廖仁義,〈從卑微的塵土到壯闊的宇宙:徐永旭陶土造形的美學意涵〉,《周流•複歌》,2012,頁6-12。
[2]「在創作的這條軸線上,選擇以『陶』材質本身的感情做為我創作的載體,以極大極薄做為這載體的形式,但我並不是要顛覆它本身或挑戰所謂的極限,而是取用了它傳統優質面的相對性,視它為相異於『陶』的『陶』,將它定義為『反陶』。」見徐永旭創作自述〈自身的逾越.創作的逾越〉。
[3]見羅薩琳.克勞斯(Rosalind Krauss)著,連德誠譯,《前衛的原創性》(The Originality of the Avant-Garde and Other Modernist Myths),臺北,遠流出版,1995,值得一提的,該書原文出版於1985年。
[4]「隱喻性的肢體」出自與徐永旭的訪談。
[5]作為「藝術文件」的作品無非貶抑了作品的自主性位階,但就如同葛羅.伊斯(Boris Groys)所稱的「藝術文件」之創作狀態,藝術卻也因此成為一種生命形式:「藝術文件標誌著在藝術空間內嘗試使用藝術的媒介去指涉生命本身,也就以生命本來的樣子指涉純粹的活動、純粹的實踐、藝術的生命,而不是直接去呈現它。藝術成為一種生命形式,藝術品變成非藝術,僅僅是這種形式的紀錄。我們也可以說藝術變成了生命政治,因為它開始使用藝術手段來生產、將生命作為一種純粹的活動來紀錄。」見葛羅.伊斯,郭昭蘭、劉文坤譯,《藝術力》,臺北,藝術家出版,2015,頁82-83。
[6]然而,根據麥可.佛理德(Michael Fried)在〈藝術與客體性〉中對極限主義表達的攻擊,這種在場感源自作品的「非藝術狀態」(the condition of non-art),在當時的藝術家口中,這種非藝術狀態形成了所謂「客體性」,而觀看這類作品的「藝術經驗則是關乎在某種情境下——幾乎是想當然爾地,是一個包含了觀者的情境——的一個客體」,佛理德接著斷言,這就是劇場性(theatricality),而劇場性是藝術的退化。該文原載於Artforum 5 (June 1967),頁 12—23。
[7]當林壽宇的鐵製作品《我們的面前是什麼》於1985年獲得「中華民國現代雕塑特展」首獎時,他曾提出:「作品任其生鏽而產生自然之美,其意在與大地永恆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