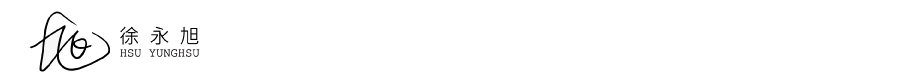2020「徙越」- 徐永旭個展
徙越
2020.10.17(六)~2020.11.28(六)
月臨畫廊 (臺中市英才路589巷6號1樓)
月臨畫廊
徐嘒壎
徙越-2020徐永旭個展
文/策展人 徐嚖壎 東海大學美術系專任助理教授
起身
這一次,不只用眼睛面對徐永旭的作品。
將身體準備好,開啟閱讀徐永旭作品的程序。首先,目光所及,場域中錯落偌大尺幅的作品,尚未決定是否依循場域動線,來做個預備動作吧。深深地吸入一口氣,意識的重心從臉部的鼻尖竄流進身體,從腹腔向胸腔散開,像是波浪一般輕輕按下著原先因奔波而略為高聳的肩膀線條。
牆上水平的壁面作品,它們如同張開臂膀一般試圖接住你。這片宽厚綿延的包覆襲捲而來,满溢於眼框之外。此時,眼睛可能正在尋找一個方法,盡收眼前的豐富。視線不停移轉,雙腳也停不下步伐,量測自身與作品之間的間隙。視覺和意識都在尋覓能暫時安歇之處。在這個進退嘗試之間,眼球與眼皮之間,輕緩地彼此按摩,即使睜眼凝視,也不覺表面乾燥,底部的雙腳在地上踩著獨特的路徑,描繪出了往返閱讀的雛形。
另一邊的垂直高聳的作品,穩健地站立於面前,腳趾在鞋子裡不自覺地微微出力抓地。這高聳的造型順勢地牽引下顎,緩緩地將頸子的薄薄皮膚拉伸向上,臉頓肌肉同時感受到一股推移舒張的力氣,這連續動作的同時作用,引發些些心理緊繃,交織成片刻的侷促和興奮,吸吐氣 之間鎖骨浮出皮層,心臟與橫隔膜之間的內凹深處輕輕顫動,或許連毛細孔都有些微癢刺麻,腳跟甚至也跟著輕微地離地。
應該覺察到了,還有更多的曲折蜿蜒在表層之下的內部。必須仰賴緩緩傾斜身子,選擇一個舒服的角度放歪脖子,感受身體兩側不同的張力,甚至耳朵都得貼齊到肩膀的程度,才能再向內觀察到一些精緻的細節。視覺正在入戲,游移在這些得來不易的情節裡。觀看的私密正在形成經驗,一種能重複播放的腦內影像。當視線朝向內部時,只有自身才能得知,到底思維跟著視線翻轉了幾個層次。當身體需要前進到下一件作品,可以不選擇同樣的路徑型態,以不同的姿勢解開身體的現有動作再抽離而出。
當觀者選擇使用身體閱讀徐永旭的作品,這些發生於身體周圍、頃刻之間的小幅度運動,可能只是一小段的序幕。身體與意識的界線在場域與作品的外部尺度之間逐漸消融,自身的運動正是一場微型的遷徙和逾越。或許,在某一個身體與意識同時運作的瞬間,觀者逐漸經驗到徐永旭創作原初狀態裡不斷堆疊的移動性。
移動
「當身體在動作,意識湧出之時我放掉意識,意識跟著我,而我還在往前跑。」一徐永旭
像是一種儀式,徐永旭時不時以慢跑作為前往工作室的移動方,,接著展開一整日約8小時的密集工作,初次聽到仿佛是台南官田的鄉野奇譚。更為奇異地,或許是徐永旭自敘裡的運動身體感。當身體處於連續運動狀態(Continuous movement),他試圖在腦內同步進行另一種動態:產生/拋丟主體意識。試著想像,在一個逐漸熱辣的南台灣清晨,這位跑者在身體和大腦進行協調之際,依然不斷趨前,行動之間冒出了汗,或許一個剎那間,今日的工作進度表也躍然於眼前,這個意識的湧出影響了身體的動作,或許突然讓腳步和呼吸失去節奏。當身體亂了調,這位跑者便隨即整頓意識,將意識作為他者,企圖把它剝離出去,並且超越在它之前。
『移動』(Mobility)實屬生命裡的常態,不單指運動(Exercises)或是物理位移(Movement)。小則日常生活中,住家與工作地點之間兩點一線、不定時的街區散步,或是一段遠途旅行,大則長距離大幅度的住宅遷徙和身份移民。這些移動之事,在結果上看到的是物理位移,,在過程中,則是一連串的節點所鏈結起的動線:移動者、移動中介、移動欲望以及移動的後續效應。徐永旭選擇以自己身體作為通勤的中介,,此舉游移在交通系統邊陲,他擁有速度的配置權,企圖獲得最程度的移動自由,並在這地表上用身體壓印出 16 公里的移動痕跡。徐永旭 似乎總是停不下來,他是一位不太慢的漫遊者。
然而,關於『移動』這件事,在2020年產生了重要的節點,迫使全球的移動暫時放慢速度。原先因移動方式便利而越來越小的世界,在2020年初春的疫情擴散之後,『移動』似乎在整體的概念上有了巨大的轉型。像是全球必須即刻下載最新的『移動』更新檔案,習以為常的方便生活和移動幅度,都被迫停止運作。身體的移動自由被削減的同時,渴求移動的集體欲望卻因此被召喚出來,能駕車出遊或是出門散步踏青,即使這樣小幅度的移動都變得彌足珍貴。如果移動的形狀能被描繪出來,過去的移動,多半仰賴大眾交通工具系統作為移動的中介, 由眾多的個體結構出部分交疊的軌跡,大部分是線性的,多向度的,造型如舒張的網,具有節點可供跳躍向外延伸。而今,因短暫的世界停滯,那個以集體移動作為交通網絡基礎,以群體現象作為社會觀察的時空速度暫緩,世界的移動版圖因此增添了更多以定點往內蜷縮的小幅度拓延,以個體自身的作為核心,向內部深掘,在集體構成的移動輪廓中,內旋出如無數洞穴般的小型陰性空間,個體內在軌跡在這個移動凝滯期被凸顯出來,如同觀者緩步在藝術品旁,正在經驗著逐漸成形的心理移動。
工作室作為藝術家的身體
在徐永旭的紀錄短片中,有段以後製拼貼複生出了無數個工作中的藝術家分身,像是時間積累的聚合物被解壓縮了一樣。從那個片段,可以進行一些想像的延伸:如果能在工作室長時間的觀察徐永旭的工作過程,把藝術家的身體看作一個黑點,日復一日的身體運動,將拖曳出一 這三維多重向度的身體軌跡造型,他的作品則隱身於這個外層建模內,像是被包覆在層層建築板模和鷹架之下。藝術家在一塊有限的工作場域面積裡,一個高溫灰色調的廠房中,他在各種臨時工作輔具之間上下爬降,水平挪移,來回往返,自我交疊。雖然說工作室像是一個廠房的型態,但藝術家的工作模式卻不同於機具的生產方式,無法看到一條逐漸由機械性的移動累積出來的軌跡。在藝術家每日創作的移動狀態裡,沒有兩條移動軌跡能完全吻合。工作室並不是一個宜人的軟性場所,處處充滿著環境變因以及人造工業配置。工作室動線,整體區域分割,硬體設施裝置以及一些細瑣的軌道零件,都是藝術家根據長久以來的工作經驗,形塑出的現行的移動習慣,再將其部署於實體空間內。 有一些結構是固定式的裝置,例如一些空間的孔洞,圓形的抽風機以相同的間距被安排在屋頂,機械扇葉的運作仰賴外界的量,時而快速旋轉,時而幾乎靜止,蛋形的動態光影以三到四個不等的扇形軌跡映照在地面,像是給了工作場所一個亂了拍子的節奏。工作室中的四座瓦斯窯,佔據相當大的面積,從窯體如小型房舍般的大小足以想像內容物的尺幅。
窯體上有許多可以觀察火的孔洞,從觀察孔洞內的變化作為燒窯時下判斷的依據。距離窯體附近通常會是較大的空礦區域,為的是給予作品迴轉移動的空間,洞口鋪設了進案的軌道,並且要時常保持地面的乾淨。主要工作區域的上方安設用來平移作品的吊掛鏈條,配合堆高機以及各式各樣藝術家自製的推台和層架,這些人造工業輔具像是與藝術家肉身鏈結的各式假肢,嫁接在藝術家的身體與意識之間,與藝術家 一同進行龐大但細膩的移動。
在工業型態的輔具環繞之下,藝術家用手部持續捏壓土條,臂膀、身軀和腳步都持續聯動。手上的土正在堆疊成造型的一部分,同時問眼前的胚體也正緩慢地隨著空氣濕度而逐漸乾燥,不能只是一直埋頭捏塑,必須同時照看土質的温度和自己身體的含水量。創作狀態時的藝術家,除了關照作品和自己的狀況,他還在想什麼呢?就像是跑步上工一樣,他正經驗移動中的身體感,當移動的程度接近生理限制的邊線,移動與勞動的界線逐漸模糊,意識與身體的運轉在交界處拼命拉扯,這些從掙扎中湧出的生命衝力,在跑步時推動著跑者,但在創作時,藝術家將它們抽離出來,以肉身的重量壓印在泥土上,作為藝術家在生命旅途裡移動的痕跡。
路徑和輿圖
作為一個移動者,徐永旭對於移動的深度實踐不只體現在跑步這件事情上。他對交通體系具有高度的敏感。從路名、方位以及各大路徑系統之間的轉換,諸如高速公路沿途的城市順序、休息站、交流道、國道、快速道路、甚至產業道路之間的切換,似乎在他腦中有一個動態的輿圖結構。這些交通系統是移動時的中介,個體駕車奔馳這些在中介上,藉由輪胎磨損的程度觀察移動者累積出來的距離總量,藉由移動中的動態視覺成就移動時的感性旋律。就算彼此目的地不同,也會有某一段的交疊,在交流道的螺旋結構體交錯而過,在休息站聚集共享暫時的停滞。交通系統形塑了社會集體的移動大輪廓,人們在移動中相遇也離散。
徐永旭的2020年新作或許可以視為各種移動的總和,像是一場盛大旅行的建構。旅行的英文是travel,旅行是一個過程,從某地移動至某地,,有一段距離的旅途。Travel 的字根是「travail ,意指『勞動』(lober)、『辛勞』。(foll之意,引申出『勞神』(trouble)、『折磨』(torture, torment)意涵。當‘Travail'作為名詞時,其中一種意思是「孕育」,另外一種意思是『勞動』。人有著移動的需求,或許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或許是一種生之衝動,隱隱推動著自己,不願長久待在原地不動。在當代,旅行的意義因著各種經濟活動、科技發展和大眾媒體的推波助瀾,轉向為一種回饋日常辛勞壓縮的集體觀光客日夢。然而,這樣的日夢其實是有節制的隨性。或許能穿著平日不能穿進辦公室的印花襯衫,拎著不能裝筆記型電腦的植物纖維編織袋,但當程序進入大眾運輸系統系統時,發車時刻的響鈴聲起,群眾被壓縮在一條黑色塑膠管子,高速傳輸般地噴射出去。群眾像是X或Y一樣,被代入一條公式裡,得出一個已知的預設途徑,目的地猶如隧道遠方的一個漂浮的發光影像,遠方的影像正在與腦中媒介化的影像記憶相互確認中,在社群媒體上滑到無數次的民宿、調酒和游泳池,終於要在眼前閃耀。但即便是如此,不管是短程或長程旅途,將身體困在一個空間有限的機殼內,以不同於日常的姿勢開車、搭車、搭飛機、或搭船,都是一種對於身體機能的耗損,更不用說過去的旅行所花費的移動時間和方式更讓肉身承受辛苦,或許這就是旅行的原義中「勞動』或是『折磨』的意味緣由。然而,仔細推敲徐永旭的創作旅途,可以發現,在他的世界裡面,沒有能持票卷搭載的便利大眾運輸系統。他是一個純然的拓荒者,寧可徒步揮汗,一寸一寸建構起自身內部朝向外部的聯通道路。
徐永旭過去的創作中,各式經典造型系列其實都指向了他生命中的關懷深刻的面向。徐永旭是個有寸度的人,做事有分寸,為人很大度。工作時的一板一眼以及明確的界線,與他平日大方熱切的模樣有著明顯的分別。他慣於將個人生命中的嚴峻、柔軟和苦甜都聽擱在作品以外,只專注於他所追求的藝術純度。我們只有在一些訪談和他者的論述中,能稍微窺見徐永旭創作以外的生命線條。但筆者以如此近距離的親屬關係身份,擔任書寫此次徐永旭個展的工作,對徐永旭的描繪是非常困難的,難以抽離出自身對他的長期觀察,也不能過於主觀地刻畫在藝術以外的徐永旭。
在經典造型中,必須先從碗殼造型的原型談起。這是他在美國駐村時,處於一種身體精神都疲倦混沌的時刻,徒手不經意捏出的元件,卻成為他近年創作重要轉捩點。筆者沒有親眼見過當時的小碗型素胚,但根據他的口述,那是一種創作者才知道的靈光乍現,當創作者在一個頃刻之間產生強烈的直覺,不需要任何其他的背書,創作者 知道這是一個像是珍寶一樣的存在,他說他小心翼翼地擺放在層架上,他知道這是必須留下的,這不起眼的小造型。在一個離家很遠的地方,有一個藝術家,他發現了一道讓自己很興奮的光線,在外面流浪很久了,這不就是他在等待的嗎?可這靈光的幅度很渺茫,無法言說,難以分享,心裏興奮地猛烈震盪,在深處的回音卻是巨大孤寂感,,對比這手中的弱造型,看著這個小碗型裡的深度,它能承接住藝術家對於自我探尋的強度嗎?這過於明顯的對比,想必在當時徐永旭心中應該相當強烈。往後,徐永旭嘗試以碗型的元件,堆疊起來形成巨大的量體,胼手胝足堆疊出來,像是集合住宅,每一戶都是一個內頃獨立空間構築了家屋群體但保有各戶之間的私密。這樣的集合體,對於他的內心來說,是一種離家很遠之後,聚集內心散逸的碎片所構築出來的巢穴嗎?
單體流線的折帶狀造型作品,則趨力度和锐度的展現,高聳但薄透的嚴峻氛圍,是藝術家針對材質與邊界的跨越。部分徐永旭創作的高聳造型作品,以強韌的生命力深根錯落在地球多處的地表上,在戶外環境中承受颱風下雨雪淋,如同藝術家意志的分身體。或許這些造型源自於藝術家個性的具體化,一種旁人不能理解、不管什麼事情都想要做到極致的瘋狂。徐永旭學生時期曾參加田徑隊,用盡體力也要在短跑比賽得名。午餐時間寧可餓著肚子,跑去樹下躲避同學便當的香味,為了省下錢買英文參考書。成年後除了白天在國小任教,徐永旭自己鑽研彈古箏很長一段時間,1984年時,分別在台北和高雄開了售票獨奏會。現在的他,在藝術創作遇到瓶頸時,會在半夜鑽研食譜,以製作功夫菜和烤蛋糕餅乾舒壓。如果不知道這些生命的軌跡,或許便難以推知徐永旭生命特質中已然存在的競爭性。那種要比從前的自 己跑在前面的欲望,在各個方面都一一顯露。
至於如奇幻藤蔓、葉片般交互纏繞的謎團物件,筆者私自認為那是藝術家個人內心某塊偏向浪漫甚至奇幻的區域。徐永旭特別喜愛植物大面積攀附的牆面,他會站在路邊聽著葉子群被風吹拂過後,伴隨風向依序譜出一陣沙沙作響。在自己家中和工作室藝術家也都會留出植物生長環繞的規劃空間。他也特別喜歡帶著奇幻色彩和科學幻想的事物,筆者年幼時曾半夜被帶往墾丁的大草原,只為了觀看獅子座流星雨。火流星劃過天際時的聲響,在空氣中拖曳出的發光軌跡,筆者至今印象深刻。徐永旭也對科學探索甚至科幻類型的戲劇非常熱衷,例 如台灣早期週末的三台,會播放《馬蓋先》(MacGyver)、《銀河飛龍》(Star Trek),筆者也從小耳濡目染這些科幻情節。
這些徐永旭生命中散落的一些事件,看似沒有關聯,但彼此都是輿圖中的重要節點。在徐永旭的性格之中,總帶著一種睿智的觀察,他會發現看似重複但相異的元件,互相堆疊交互作用後,將產生一種質變。相信人的意志能跨越既有的限制,這樣的特質形塑出一位質樸的、靈活的但努力踏實的實踐者。
視野和秘境
從 2019年末,徐永旭的作品中開始出現了一些造型轉向的視野。 2020年的「徙越』個展作品中,我們能觀察到這個轉向以更明朗方式向我們說話。不僅在雕塑造型上的轉型,藝術家在思維形態上的遷徙和越出可以從作品中探知。大面積的寬面土層從底下經典的碗型結構中悄然脫出,豪邁地大面積鋪蓋、翻折與交錯在繁密的單顆碗型反覆重疊的群體上。那是一條條由大拇指推壓出的肌理累積而出的路,絕對不是一條坦途,下方支撑路面 是具有空隙的碗型結構,像是在底下累積著溫厚的存在,一絲僻靜與安穩安放於此。偶爾從路面底下會竄出羊腸小徑和排水溝渠,讓視覺即心理上的衝力得以暫時往內躲藏和停歇。寬闊的主要道路之間,時有一些橋樑和開道互通,那往往是觀眾用目光游移在作品上時,交換視線、轉換目光之處,像是高速公路的交流道 一樣串連各方的節點形成網絡。
從本文的一開始,筆者便邀請觀眾一同試著用身體感受徐永旭的新作。徐永旭的作品不只為了個人移動的需求,他鋪設了層層坡面,架起了溝通互通的橋樑,在在都顯示了預留了觀眾前來共享風景的開放性。試著將觀看作品想像為一次的旅行。從遠處觀望時,像是以俯瞰視角觀望著一幅遼闊輿圖,當你試圖停留在作品旁,與其相處更久一段時間,找尋一個想去的地方,按圖索驥,拉近距離,你會逐漸依隨身體的選擇,找到一條特殊的路徑,在視覺移動的過程感受藝術家建構的旅程,感受因想像而移動的心智,仿若移至他鄉,初見異地,心裡既不安但興奮。
單體作品承襲了建築物的想像,延伸出諸多像是螺旋梯和細密隔間 一般的片狀體,鏤空的結構讓觀看更具有靈活度,彷彿秘境就近在咫尺。
徙越
徐永旭的『徙越』,不是寄望著到達目標的『喜悅』時刻。而是在每個移動時刻,每一次的運動鍛鍊也好,每一次的創作體悟也好,藝術家總是不間斷地尋求一種內外動態平衡。一種能精準控制移動幅度的輕盈狀態,游移在精神、身體與環繞於外的事物之間。這需要長期與自我深刻談話,尤其當外在事物的各種不均衡讓生活粗糙,藝術家在自我鍛鍊的過程中,需要找到讓他優雅以對的方式。
從某些視角的觀點看到的徐永旭,似乎呈現出一種悲壯。藝術家的肉身苦痛重複堆積,作品成為勞動實體化的結果。在某些情況下的描述,以乎讓藝術家本身的生命經驗凌駕於作品本身能帶給觀眾的精神向度。筆者在此次的策展思考中,試圖提出另外一種角度的觀點。當前的徐永旭,應該依然在工作室裡揮灑汗水,忙忙進忙出,大部分時間埋首著手上的工作,但不時也得處理訊息量巨大的各種細瑣事項。然而,在心境和對身體的掌握,徐永旭似乎不斷地進行自我鬆綁, 自我逾越,自我愉悦。或許是從這幾年接觸慢跑所累積的心得,或許是時間的經過給出了體悟的契機。只要持續移動著,不管快慢,風景都會在身旁逐漸地湧現(emerging}。如同捏塑陶土的同時,手中的陶土正在從物體成為作品 (becoming artwork),徐永旭沈浸於每一個頃刻的風景,以及每一個陶土逐漸成為作品的當下。這是藝術家創作狀態中的機密蘊育過程,也是藝術家找到讓自己往前移動的微小觸動,徐永旭的「徙越』就是從這些不為人知的頃刻累積而來。這樣的勤懇踏實,當然能稱為身體勞動,但藉由身體反覆挪移,像是每一次的運動鍛鍊, 在身體的破壞與新生之間,如新陳代謝般循環,這些連鎖的後續效應同步伴隨徐永旭,構築著即將前往某處的路徑。或許,作為觀眾的你已 經覺察到,在每一次靠近徐永旭作品的展出現場,如果不急著得知關於作品的周邊資訊,先讓身體帶著直覺靠近,會慢慢地發現那個一直以 為在遠方的秘境,其實已經同步顯現於觀者相遇作品時的每個當下。
2020.10.17(六)~2020.11.28(六)
月臨畫廊 (臺中市英才路589巷6號1樓)
月臨畫廊
徐嘒壎
徙越-2020徐永旭個展
文/策展人 徐嚖壎 東海大學美術系專任助理教授
起身
這一次,不只用眼睛面對徐永旭的作品。
將身體準備好,開啟閱讀徐永旭作品的程序。首先,目光所及,場域中錯落偌大尺幅的作品,尚未決定是否依循場域動線,來做個預備動作吧。深深地吸入一口氣,意識的重心從臉部的鼻尖竄流進身體,從腹腔向胸腔散開,像是波浪一般輕輕按下著原先因奔波而略為高聳的肩膀線條。
牆上水平的壁面作品,它們如同張開臂膀一般試圖接住你。這片宽厚綿延的包覆襲捲而來,满溢於眼框之外。此時,眼睛可能正在尋找一個方法,盡收眼前的豐富。視線不停移轉,雙腳也停不下步伐,量測自身與作品之間的間隙。視覺和意識都在尋覓能暫時安歇之處。在這個進退嘗試之間,眼球與眼皮之間,輕緩地彼此按摩,即使睜眼凝視,也不覺表面乾燥,底部的雙腳在地上踩著獨特的路徑,描繪出了往返閱讀的雛形。
另一邊的垂直高聳的作品,穩健地站立於面前,腳趾在鞋子裡不自覺地微微出力抓地。這高聳的造型順勢地牽引下顎,緩緩地將頸子的薄薄皮膚拉伸向上,臉頓肌肉同時感受到一股推移舒張的力氣,這連續動作的同時作用,引發些些心理緊繃,交織成片刻的侷促和興奮,吸吐氣 之間鎖骨浮出皮層,心臟與橫隔膜之間的內凹深處輕輕顫動,或許連毛細孔都有些微癢刺麻,腳跟甚至也跟著輕微地離地。
應該覺察到了,還有更多的曲折蜿蜒在表層之下的內部。必須仰賴緩緩傾斜身子,選擇一個舒服的角度放歪脖子,感受身體兩側不同的張力,甚至耳朵都得貼齊到肩膀的程度,才能再向內觀察到一些精緻的細節。視覺正在入戲,游移在這些得來不易的情節裡。觀看的私密正在形成經驗,一種能重複播放的腦內影像。當視線朝向內部時,只有自身才能得知,到底思維跟著視線翻轉了幾個層次。當身體需要前進到下一件作品,可以不選擇同樣的路徑型態,以不同的姿勢解開身體的現有動作再抽離而出。
當觀者選擇使用身體閱讀徐永旭的作品,這些發生於身體周圍、頃刻之間的小幅度運動,可能只是一小段的序幕。身體與意識的界線在場域與作品的外部尺度之間逐漸消融,自身的運動正是一場微型的遷徙和逾越。或許,在某一個身體與意識同時運作的瞬間,觀者逐漸經驗到徐永旭創作原初狀態裡不斷堆疊的移動性。
移動
「當身體在動作,意識湧出之時我放掉意識,意識跟著我,而我還在往前跑。」一徐永旭
像是一種儀式,徐永旭時不時以慢跑作為前往工作室的移動方,,接著展開一整日約8小時的密集工作,初次聽到仿佛是台南官田的鄉野奇譚。更為奇異地,或許是徐永旭自敘裡的運動身體感。當身體處於連續運動狀態(Continuous movement),他試圖在腦內同步進行另一種動態:產生/拋丟主體意識。試著想像,在一個逐漸熱辣的南台灣清晨,這位跑者在身體和大腦進行協調之際,依然不斷趨前,行動之間冒出了汗,或許一個剎那間,今日的工作進度表也躍然於眼前,這個意識的湧出影響了身體的動作,或許突然讓腳步和呼吸失去節奏。當身體亂了調,這位跑者便隨即整頓意識,將意識作為他者,企圖把它剝離出去,並且超越在它之前。
『移動』(Mobility)實屬生命裡的常態,不單指運動(Exercises)或是物理位移(Movement)。小則日常生活中,住家與工作地點之間兩點一線、不定時的街區散步,或是一段遠途旅行,大則長距離大幅度的住宅遷徙和身份移民。這些移動之事,在結果上看到的是物理位移,,在過程中,則是一連串的節點所鏈結起的動線:移動者、移動中介、移動欲望以及移動的後續效應。徐永旭選擇以自己身體作為通勤的中介,,此舉游移在交通系統邊陲,他擁有速度的配置權,企圖獲得最程度的移動自由,並在這地表上用身體壓印出 16 公里的移動痕跡。徐永旭 似乎總是停不下來,他是一位不太慢的漫遊者。
然而,關於『移動』這件事,在2020年產生了重要的節點,迫使全球的移動暫時放慢速度。原先因移動方式便利而越來越小的世界,在2020年初春的疫情擴散之後,『移動』似乎在整體的概念上有了巨大的轉型。像是全球必須即刻下載最新的『移動』更新檔案,習以為常的方便生活和移動幅度,都被迫停止運作。身體的移動自由被削減的同時,渴求移動的集體欲望卻因此被召喚出來,能駕車出遊或是出門散步踏青,即使這樣小幅度的移動都變得彌足珍貴。如果移動的形狀能被描繪出來,過去的移動,多半仰賴大眾交通工具系統作為移動的中介, 由眾多的個體結構出部分交疊的軌跡,大部分是線性的,多向度的,造型如舒張的網,具有節點可供跳躍向外延伸。而今,因短暫的世界停滯,那個以集體移動作為交通網絡基礎,以群體現象作為社會觀察的時空速度暫緩,世界的移動版圖因此增添了更多以定點往內蜷縮的小幅度拓延,以個體自身的作為核心,向內部深掘,在集體構成的移動輪廓中,內旋出如無數洞穴般的小型陰性空間,個體內在軌跡在這個移動凝滯期被凸顯出來,如同觀者緩步在藝術品旁,正在經驗著逐漸成形的心理移動。
工作室作為藝術家的身體
在徐永旭的紀錄短片中,有段以後製拼貼複生出了無數個工作中的藝術家分身,像是時間積累的聚合物被解壓縮了一樣。從那個片段,可以進行一些想像的延伸:如果能在工作室長時間的觀察徐永旭的工作過程,把藝術家的身體看作一個黑點,日復一日的身體運動,將拖曳出一 這三維多重向度的身體軌跡造型,他的作品則隱身於這個外層建模內,像是被包覆在層層建築板模和鷹架之下。藝術家在一塊有限的工作場域面積裡,一個高溫灰色調的廠房中,他在各種臨時工作輔具之間上下爬降,水平挪移,來回往返,自我交疊。雖然說工作室像是一個廠房的型態,但藝術家的工作模式卻不同於機具的生產方式,無法看到一條逐漸由機械性的移動累積出來的軌跡。在藝術家每日創作的移動狀態裡,沒有兩條移動軌跡能完全吻合。工作室並不是一個宜人的軟性場所,處處充滿著環境變因以及人造工業配置。工作室動線,整體區域分割,硬體設施裝置以及一些細瑣的軌道零件,都是藝術家根據長久以來的工作經驗,形塑出的現行的移動習慣,再將其部署於實體空間內。 有一些結構是固定式的裝置,例如一些空間的孔洞,圓形的抽風機以相同的間距被安排在屋頂,機械扇葉的運作仰賴外界的量,時而快速旋轉,時而幾乎靜止,蛋形的動態光影以三到四個不等的扇形軌跡映照在地面,像是給了工作場所一個亂了拍子的節奏。工作室中的四座瓦斯窯,佔據相當大的面積,從窯體如小型房舍般的大小足以想像內容物的尺幅。
窯體上有許多可以觀察火的孔洞,從觀察孔洞內的變化作為燒窯時下判斷的依據。距離窯體附近通常會是較大的空礦區域,為的是給予作品迴轉移動的空間,洞口鋪設了進案的軌道,並且要時常保持地面的乾淨。主要工作區域的上方安設用來平移作品的吊掛鏈條,配合堆高機以及各式各樣藝術家自製的推台和層架,這些人造工業輔具像是與藝術家肉身鏈結的各式假肢,嫁接在藝術家的身體與意識之間,與藝術家 一同進行龐大但細膩的移動。
在工業型態的輔具環繞之下,藝術家用手部持續捏壓土條,臂膀、身軀和腳步都持續聯動。手上的土正在堆疊成造型的一部分,同時問眼前的胚體也正緩慢地隨著空氣濕度而逐漸乾燥,不能只是一直埋頭捏塑,必須同時照看土質的温度和自己身體的含水量。創作狀態時的藝術家,除了關照作品和自己的狀況,他還在想什麼呢?就像是跑步上工一樣,他正經驗移動中的身體感,當移動的程度接近生理限制的邊線,移動與勞動的界線逐漸模糊,意識與身體的運轉在交界處拼命拉扯,這些從掙扎中湧出的生命衝力,在跑步時推動著跑者,但在創作時,藝術家將它們抽離出來,以肉身的重量壓印在泥土上,作為藝術家在生命旅途裡移動的痕跡。
路徑和輿圖
作為一個移動者,徐永旭對於移動的深度實踐不只體現在跑步這件事情上。他對交通體系具有高度的敏感。從路名、方位以及各大路徑系統之間的轉換,諸如高速公路沿途的城市順序、休息站、交流道、國道、快速道路、甚至產業道路之間的切換,似乎在他腦中有一個動態的輿圖結構。這些交通系統是移動時的中介,個體駕車奔馳這些在中介上,藉由輪胎磨損的程度觀察移動者累積出來的距離總量,藉由移動中的動態視覺成就移動時的感性旋律。就算彼此目的地不同,也會有某一段的交疊,在交流道的螺旋結構體交錯而過,在休息站聚集共享暫時的停滞。交通系統形塑了社會集體的移動大輪廓,人們在移動中相遇也離散。
徐永旭的2020年新作或許可以視為各種移動的總和,像是一場盛大旅行的建構。旅行的英文是travel,旅行是一個過程,從某地移動至某地,,有一段距離的旅途。Travel 的字根是「travail ,意指『勞動』(lober)、『辛勞』。(foll之意,引申出『勞神』(trouble)、『折磨』(torture, torment)意涵。當‘Travail'作為名詞時,其中一種意思是「孕育」,另外一種意思是『勞動』。人有著移動的需求,或許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或許是一種生之衝動,隱隱推動著自己,不願長久待在原地不動。在當代,旅行的意義因著各種經濟活動、科技發展和大眾媒體的推波助瀾,轉向為一種回饋日常辛勞壓縮的集體觀光客日夢。然而,這樣的日夢其實是有節制的隨性。或許能穿著平日不能穿進辦公室的印花襯衫,拎著不能裝筆記型電腦的植物纖維編織袋,但當程序進入大眾運輸系統系統時,發車時刻的響鈴聲起,群眾被壓縮在一條黑色塑膠管子,高速傳輸般地噴射出去。群眾像是X或Y一樣,被代入一條公式裡,得出一個已知的預設途徑,目的地猶如隧道遠方的一個漂浮的發光影像,遠方的影像正在與腦中媒介化的影像記憶相互確認中,在社群媒體上滑到無數次的民宿、調酒和游泳池,終於要在眼前閃耀。但即便是如此,不管是短程或長程旅途,將身體困在一個空間有限的機殼內,以不同於日常的姿勢開車、搭車、搭飛機、或搭船,都是一種對於身體機能的耗損,更不用說過去的旅行所花費的移動時間和方式更讓肉身承受辛苦,或許這就是旅行的原義中「勞動』或是『折磨』的意味緣由。然而,仔細推敲徐永旭的創作旅途,可以發現,在他的世界裡面,沒有能持票卷搭載的便利大眾運輸系統。他是一個純然的拓荒者,寧可徒步揮汗,一寸一寸建構起自身內部朝向外部的聯通道路。
徐永旭過去的創作中,各式經典造型系列其實都指向了他生命中的關懷深刻的面向。徐永旭是個有寸度的人,做事有分寸,為人很大度。工作時的一板一眼以及明確的界線,與他平日大方熱切的模樣有著明顯的分別。他慣於將個人生命中的嚴峻、柔軟和苦甜都聽擱在作品以外,只專注於他所追求的藝術純度。我們只有在一些訪談和他者的論述中,能稍微窺見徐永旭創作以外的生命線條。但筆者以如此近距離的親屬關係身份,擔任書寫此次徐永旭個展的工作,對徐永旭的描繪是非常困難的,難以抽離出自身對他的長期觀察,也不能過於主觀地刻畫在藝術以外的徐永旭。
在經典造型中,必須先從碗殼造型的原型談起。這是他在美國駐村時,處於一種身體精神都疲倦混沌的時刻,徒手不經意捏出的元件,卻成為他近年創作重要轉捩點。筆者沒有親眼見過當時的小碗型素胚,但根據他的口述,那是一種創作者才知道的靈光乍現,當創作者在一個頃刻之間產生強烈的直覺,不需要任何其他的背書,創作者 知道這是一個像是珍寶一樣的存在,他說他小心翼翼地擺放在層架上,他知道這是必須留下的,這不起眼的小造型。在一個離家很遠的地方,有一個藝術家,他發現了一道讓自己很興奮的光線,在外面流浪很久了,這不就是他在等待的嗎?可這靈光的幅度很渺茫,無法言說,難以分享,心裏興奮地猛烈震盪,在深處的回音卻是巨大孤寂感,,對比這手中的弱造型,看著這個小碗型裡的深度,它能承接住藝術家對於自我探尋的強度嗎?這過於明顯的對比,想必在當時徐永旭心中應該相當強烈。往後,徐永旭嘗試以碗型的元件,堆疊起來形成巨大的量體,胼手胝足堆疊出來,像是集合住宅,每一戶都是一個內頃獨立空間構築了家屋群體但保有各戶之間的私密。這樣的集合體,對於他的內心來說,是一種離家很遠之後,聚集內心散逸的碎片所構築出來的巢穴嗎?
單體流線的折帶狀造型作品,則趨力度和锐度的展現,高聳但薄透的嚴峻氛圍,是藝術家針對材質與邊界的跨越。部分徐永旭創作的高聳造型作品,以強韌的生命力深根錯落在地球多處的地表上,在戶外環境中承受颱風下雨雪淋,如同藝術家意志的分身體。或許這些造型源自於藝術家個性的具體化,一種旁人不能理解、不管什麼事情都想要做到極致的瘋狂。徐永旭學生時期曾參加田徑隊,用盡體力也要在短跑比賽得名。午餐時間寧可餓著肚子,跑去樹下躲避同學便當的香味,為了省下錢買英文參考書。成年後除了白天在國小任教,徐永旭自己鑽研彈古箏很長一段時間,1984年時,分別在台北和高雄開了售票獨奏會。現在的他,在藝術創作遇到瓶頸時,會在半夜鑽研食譜,以製作功夫菜和烤蛋糕餅乾舒壓。如果不知道這些生命的軌跡,或許便難以推知徐永旭生命特質中已然存在的競爭性。那種要比從前的自 己跑在前面的欲望,在各個方面都一一顯露。
至於如奇幻藤蔓、葉片般交互纏繞的謎團物件,筆者私自認為那是藝術家個人內心某塊偏向浪漫甚至奇幻的區域。徐永旭特別喜愛植物大面積攀附的牆面,他會站在路邊聽著葉子群被風吹拂過後,伴隨風向依序譜出一陣沙沙作響。在自己家中和工作室藝術家也都會留出植物生長環繞的規劃空間。他也特別喜歡帶著奇幻色彩和科學幻想的事物,筆者年幼時曾半夜被帶往墾丁的大草原,只為了觀看獅子座流星雨。火流星劃過天際時的聲響,在空氣中拖曳出的發光軌跡,筆者至今印象深刻。徐永旭也對科學探索甚至科幻類型的戲劇非常熱衷,例 如台灣早期週末的三台,會播放《馬蓋先》(MacGyver)、《銀河飛龍》(Star Trek),筆者也從小耳濡目染這些科幻情節。
這些徐永旭生命中散落的一些事件,看似沒有關聯,但彼此都是輿圖中的重要節點。在徐永旭的性格之中,總帶著一種睿智的觀察,他會發現看似重複但相異的元件,互相堆疊交互作用後,將產生一種質變。相信人的意志能跨越既有的限制,這樣的特質形塑出一位質樸的、靈活的但努力踏實的實踐者。
視野和秘境
從 2019年末,徐永旭的作品中開始出現了一些造型轉向的視野。 2020年的「徙越』個展作品中,我們能觀察到這個轉向以更明朗方式向我們說話。不僅在雕塑造型上的轉型,藝術家在思維形態上的遷徙和越出可以從作品中探知。大面積的寬面土層從底下經典的碗型結構中悄然脫出,豪邁地大面積鋪蓋、翻折與交錯在繁密的單顆碗型反覆重疊的群體上。那是一條條由大拇指推壓出的肌理累積而出的路,絕對不是一條坦途,下方支撑路面 是具有空隙的碗型結構,像是在底下累積著溫厚的存在,一絲僻靜與安穩安放於此。偶爾從路面底下會竄出羊腸小徑和排水溝渠,讓視覺即心理上的衝力得以暫時往內躲藏和停歇。寬闊的主要道路之間,時有一些橋樑和開道互通,那往往是觀眾用目光游移在作品上時,交換視線、轉換目光之處,像是高速公路的交流道 一樣串連各方的節點形成網絡。
從本文的一開始,筆者便邀請觀眾一同試著用身體感受徐永旭的新作。徐永旭的作品不只為了個人移動的需求,他鋪設了層層坡面,架起了溝通互通的橋樑,在在都顯示了預留了觀眾前來共享風景的開放性。試著將觀看作品想像為一次的旅行。從遠處觀望時,像是以俯瞰視角觀望著一幅遼闊輿圖,當你試圖停留在作品旁,與其相處更久一段時間,找尋一個想去的地方,按圖索驥,拉近距離,你會逐漸依隨身體的選擇,找到一條特殊的路徑,在視覺移動的過程感受藝術家建構的旅程,感受因想像而移動的心智,仿若移至他鄉,初見異地,心裡既不安但興奮。
單體作品承襲了建築物的想像,延伸出諸多像是螺旋梯和細密隔間 一般的片狀體,鏤空的結構讓觀看更具有靈活度,彷彿秘境就近在咫尺。
徙越
徐永旭的『徙越』,不是寄望著到達目標的『喜悅』時刻。而是在每個移動時刻,每一次的運動鍛鍊也好,每一次的創作體悟也好,藝術家總是不間斷地尋求一種內外動態平衡。一種能精準控制移動幅度的輕盈狀態,游移在精神、身體與環繞於外的事物之間。這需要長期與自我深刻談話,尤其當外在事物的各種不均衡讓生活粗糙,藝術家在自我鍛鍊的過程中,需要找到讓他優雅以對的方式。
從某些視角的觀點看到的徐永旭,似乎呈現出一種悲壯。藝術家的肉身苦痛重複堆積,作品成為勞動實體化的結果。在某些情況下的描述,以乎讓藝術家本身的生命經驗凌駕於作品本身能帶給觀眾的精神向度。筆者在此次的策展思考中,試圖提出另外一種角度的觀點。當前的徐永旭,應該依然在工作室裡揮灑汗水,忙忙進忙出,大部分時間埋首著手上的工作,但不時也得處理訊息量巨大的各種細瑣事項。然而,在心境和對身體的掌握,徐永旭似乎不斷地進行自我鬆綁, 自我逾越,自我愉悦。或許是從這幾年接觸慢跑所累積的心得,或許是時間的經過給出了體悟的契機。只要持續移動著,不管快慢,風景都會在身旁逐漸地湧現(emerging}。如同捏塑陶土的同時,手中的陶土正在從物體成為作品 (becoming artwork),徐永旭沈浸於每一個頃刻的風景,以及每一個陶土逐漸成為作品的當下。這是藝術家創作狀態中的機密蘊育過程,也是藝術家找到讓自己往前移動的微小觸動,徐永旭的「徙越』就是從這些不為人知的頃刻累積而來。這樣的勤懇踏實,當然能稱為身體勞動,但藉由身體反覆挪移,像是每一次的運動鍛鍊, 在身體的破壞與新生之間,如新陳代謝般循環,這些連鎖的後續效應同步伴隨徐永旭,構築著即將前往某處的路徑。或許,作為觀眾的你已 經覺察到,在每一次靠近徐永旭作品的展出現場,如果不急著得知關於作品的周邊資訊,先讓身體帶著直覺靠近,會慢慢地發現那個一直以 為在遠方的秘境,其實已經同步顯現於觀者相遇作品時的每個當下。